西方戏剧史:17 世纪至今/法国二战后

让-保罗·萨特在之前时期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了《阿尔托纳的禁闭》(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阿尔托纳的被禁闭者》,1959 年)。
《阿尔托纳的禁闭》“探讨了罪恶:确定罪恶从何开始,罪恶归属于何处,罪恶在何处(以及是否)终结...这部戏剧试图将良知的生活,道德热情的生命,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调和起来,即如果任何罪行都被追溯到其逻辑根源,罪犯并不孤单。在每一次不道德的行为背后,总有社会、心理或历史上的原因,它又通向另一个原因,然后又通向其他原因,远离罪犯本身。但是,萨特问道,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像必须那样去评判呢?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善?我们如何才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更易于忍受?萨特为他的主题选择的戏剧意象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夫曼,2021,第 23 页)。“萨特在《阿尔托纳的禁闭者》中出现的另一个关注点是,胜利者是失败者,而失败者则是胜利者。父亲成功地见到了弗朗茨,却发现他们之间无法交流。勒妮毁掉了约翰娜和弗朗茨之间的关系,却完全失去了他”(奥康纳,1975 年,第 31 页)。
“在冯·格拉赫家中...时间停止了,因为弗朗茨...他从未对决定性行为负起责任,直到有一天在斯摩棱斯克,他折磨了一名游击队员。据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国家,但实际上是为了克服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断言他对父亲的独立性,并通过一项重大行为来表现自己的个人力量”(杰克逊,1965 年,第 64 页)。“这些人物都完全意识到他们处于虚伪状态,并有意识地选择继续这样...虚伪在于用一个角色取代个性...正如勒妮所说,'你知道,我们玩的是输家通吃的游戏'...她试图让弗朗茨直面他的过去...她失败了...[并且] 只是想演好她选择的角色,她对改变现状没有任何兴趣...她的态度概括在她乱伦的关系中...勒妮选择成为...一个失败的叛逆者...[因为] 失败只需要被渴望就会被转化为成功...只有当[弗朗茨] 保持自我禁闭时,她才能利用他作为武器来对付她的父亲,并在她对家庭所代表的一切的象征性叛逆中。对于维尔纳来说,约翰娜与弗朗茨的关系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后的侮辱,[它] 不那么依赖维尔纳与妻子的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两个兄弟之间以及他们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什么都不想比取悦他父亲更好...但他总是受到阻挠...正如勒妮和维尔纳选择成为失败者一样,约翰娜也是如此...约翰娜的婚礼是她本质上的美丽葬礼...然而,她需要一个观众来见证她的殉道:维尔纳...格拉赫生活中驱动力一直是对资本主义力量的正直的信念...[他] 漠视了对纳粹权力性质的所有正常反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在于没有可见的替代方案...[在自杀中] 是选择自己失败方式的可能性...为什么弗朗茨对谋杀和酷刑感到内疚?...[他] 感到厌恶,因为他无力做任何其他事情...他是有良知的...但主要的欲望是权力...他的恳求是,历史进程的本质是,邪恶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可能结果...他暗示了自己的罪恶,而罪恶假设了自由”(帕尔默,1988 年,第 308-317 页)。“弗朗茨不仅发现了自己的不真实和无能,而且以一种尖锐的形式体验到了被锤入地面的主观状态。只有一件事,他不是他父亲的镜像,那就是当他使用酷刑时,所以死亡是他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的唯一方法——意识到他白白地酷刑——并断言他自身现实中所剩无几的东西”(沃德曼,1992 年,第 263 页)。
“弗朗茨把自己禁闭起来,是因为他过去参与了战争罪行,目前也参与了乱伦...勒妮对哥哥的爱...在她哥哥更直接的禁闭的封闭氛围中蓬勃发展。为了保护这种亲密关系,她多年来一直拒绝做她父亲的使者。此外,勒妮意识到,她对哥哥的爱是她狂热地拥护某种部落家庭生活准则的一部分。'乱伦是我让家庭关系更加紧密的方式,'她说...维尔纳天生就嫉妒。被弗朗茨取代,维尔纳无法投入任何关系,除非是对他父亲一直以来的永久追求的态度...问题是:为什么他不肯离开?他...根植于自己对自卑的信念...乍一看,约翰娜似乎是一个精力充沛、平衡的女人,准备为她的丈夫而战...她与其说是同谋,不如说是受害者...她已经朝着自己的个体解放前进...这就是维尔纳不理解她的地方,而通过他的不理解,他把她判处了她已经放弃的虚构世界...老格拉赫禁闭了所有人...如果他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自己是最大的'禁闭者'...他的唯一道德准则是目的 оправдывает средства...他说纳粹:'我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为我服务...但他们正在打仗,为了给我们寻找市场,我将在一块土地上与他们发生冲突'...弗朗茨禁闭综合症的根源”(普奇亚尼,1961 年,第 23-30 页)。“恐惧是专横的家父与子女之间唯一的感情纽带,约翰娜发现他无法爱导致了他的妻子死亡。在情感上和身体上拒绝了他的小儿子,冯·格拉赫长子让维尔纳成为了他虐待的主要目标。同样的缺乏感情让他与女儿的感情隔绝”(加勒,1971 年,第 179 页)。
“五个角色的存在主要为了弗朗茨,他的禁闭也禁闭了他们...格拉赫与纳粹的勾结是基于纳粹权力的现实;保持老板的身份是首要的,在战争期间保持老板身份意味着与希特勒合作...当剧目开始时...格拉赫仍然拥有形式,但不再指挥它...弗朗茨的出生和成长是为了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老板,拥有他父亲的骄傲和他的父亲的激情...三年来,他的父亲一直知道他是'斯摩棱斯克的屠夫'。然而,冯·格拉赫既不能也不愿评判他的儿子。与弗朗茨无论他是什么样的都绑定在一起,冯·格拉赫拒绝了弗朗茨的行为,但他仍然完全爱着他。他的父爱,源于身份,使判断成为不可能。当冯·格拉赫承担了弗朗茨作为斯摩棱斯克屠夫的罪行的责任时,父子之间的身份得到了解决。弗朗茨一无所有,他允许他的父亲神圣化那种虚无”(麦考尔,1969 年,第 128-139 页)。“可以推测,在弗朗茨的半清醒意识中,[天花板上看到的] 非人性的甲壳类动物代表着地球未来的居民,是即将搞砸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的人类的继承者”(帕塞尔,1986d 年,第 1651 页)。
“弗朗茨的一生都被他父亲的决定所扭曲,他父亲决定倾尽一切,包括自己的孩子,去打造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布拉德比,1991 年,第 44 页)。“剧本的结尾,父子俩驾着保时捷从魔鬼桥上跳下自杀,象征着父亲共谋行为的破产,以及儿子最终的道德无力。然而,观众也被卷入其中,因为他们被迫在死后聆听弗朗茨的预录讲话——一种由已故主角创作的倒叙,但却是针对观众的;这也是从过去回溯到现在和未来以澄清事态的另一个例子。在讲话中,弗朗茨宣称‘如果人类没有被其残酷、古老的敌人追赶,这个世纪本来会很好,那个发誓要毁灭人类的食肉物种,那个凶残的无毛野兽——人’。该剧的最后时刻也包含了《苍蝇》(1943 年)和《无出口》(1944 年)的一些元素。弗朗茨用类似俄瑞斯忒斯的姿态,承担起这个世界的责任,‘将这个世纪扛在他的肩上’,而与《无出口》一样,该剧没有戛然而止。故事并没有结束……‘莱妮走进他的房间’”,于是成为冯·格拉赫企业下一个囚徒,而这个企业将由维尔纳在妻子约翰娜的帮助下继续经营(范登·霍芬,2012 年,第 69-70 页)。
约翰娜“是最不隐蔽的人,最害怕成为囚徒;她是唯一一个看穿虚假的人,包括她自己以前作为电影明星的虚假身份。维尔纳,一个健壮的体格却性格软弱的人,似乎主要感兴趣的是想从他父亲那里,迟来的,得到他从未得到过的认可,作为一个小儿子”(布罗斯曼,1983 年,第 95 页)。
"隔离在阿尔托纳"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地点:德国汉堡的阿尔托纳区。
文本在?
得知自己只剩几个月可活后,一位实业家冯·格拉赫希望他的小儿子维尔纳接管他的造船生意。他还要求维尔纳、他的妻子约翰娜和他的妹妹莱妮留在他们 32 间房的家族豪宅里,照看他的大儿子弗朗茨,弗朗茨已经被隔离在这个房子里 13 年了。维尔纳和莱妮同意这样做,但约翰娜想独自搬到其他地方,这样父亲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三个人在他死后还要待在一起。1941 年,他收到纳粹部长戈培尔的提议,让他出售自己的田地,并为犹太人建立一个集中营,他接受了。在对犹太人的迫害中,弗朗茨被发现私藏了一名拉比在父亲的豪宅里。这名拉比被党卫军官兵当着弗朗茨的面杀害,格拉赫被迫把儿子送到俄国战线。约翰娜怀疑是她丈夫向党卫军通风报信。1946 年,美国军官被邀请到豪宅,在那里,莱妮习惯于激起他们的欲望,然后用侮辱的话语打消他们的念头。有一天,一名军官试图强奸她。她用瓶子击打军官的头部,成功地自卫了。为了保护她免受因这件事被追究责任,弗朗茨承担了罪责,并通过与一名美军将军的交易,被允许出国,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躲藏起来。约翰娜讨厌这个故事。她没有改变主意,向丈夫发出最后通牒:要么留下来,要么跟着她去其他地方。多年来,弗朗茨拒绝见父亲,只允许莱妮进入他的房间。格拉赫试图说服约翰娜与弗朗茨谈谈,至少让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弗朗茨并不是他父亲故事中描述的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他穿着破损的军官制服,在房间里放着希特勒的画像,并在上面撒满了牡蛎壳。自战争结束后,他认为整个国家都被杂草淹没,要么醉酒消遣,要么与姐姐发生乱伦关系。约翰娜从丈夫那里得到了莱妮的秘密密码,去看弗朗茨。她告诉弗朗茨,他父亲快死了,她宁愿看到他自由或死亡,也不愿看到他这样生活。在得知约翰娜成功地见到了弗朗茨之后,格拉赫也要求见他,但约翰娜拒绝帮忙,她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他死亡。维尔纳认为父亲的目的是让弗朗茨接管他的生意。最终,约翰娜改变了主意,告诉弗朗茨他父亲想见他,但无法诱使他回到正常的生活。“我将立刻放弃我的虚幻生活……当我比我的谎言更爱你,当你尽管知道我的真相却仍然爱我时”,弗朗茨宣称。他明确表示,他被隔离并非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他被动地允许他手下的一名狂热士兵折磨了一些平民。他的坦白,在莱妮嫉妒竞争对手的刺激下,让约翰娜感到厌恶。约翰娜和莱妮都无法说服弗朗茨离开房间。然而,就在约翰娜从他们之间开始萌发的爱情中退却的那一刻,他终于同意见他的父亲。弗朗茨在报纸上读到他父亲的财务成功,他一直都在玩“输者赢”的游戏。格拉赫惊讶地发现弗朗茨同意接管生意。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弗朗茨提醒他,他们曾经一起高速驾驶汽车,两人都希望重温那段经历。当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莱妮确信他们会一起死去。
亨利·德·蒙泰朗
[edit | edit source]
亨利·德·蒙泰朗(1895-1972 年)在之前时期之后,又创作了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延续了现实主义呈现历史的传统,即“圣地亚哥之主”(The master of Santiago,1948 年)。
在“圣地亚哥之主”中,“一位父亲拒绝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女儿与她心爱的人的完美婚姻,因为他拒绝与西班牙在摩尔人战败后舒适繁荣和权势熏心的生活中妥协。他的女儿,受到父亲极度高尚的品格的激励,结束了这场本可以为他带来财富,并让她得以结婚的骗局。这位父亲是一位非凡而逼真的唐吉诃德(尽管没有荒诞的属性),他对阴谋诡计的世界以及西班牙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的厌恶,达到了真正英雄的程度。这部戏剧中理想主义的火焰无处不在。人们只能希望它也有更多的人性温暖。这位骑士几乎超人的纯粹动机,无疑是要给普通人——蒙泰朗也许过于轻蔑他们而无法成为真正伟大的剧作家——一记耳光”(加斯纳,1954a 年,第 724 页)。这出戏的宏伟规模“采取了抵抗的形式,用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对任何庸俗、平庸、平常事物的不满”(克鲁克香克,1964 年,第 110 页)。
“唐·阿尔瓦罗,他的使命是将新世界的印第安人改宗,蔑视着他所引导的努力……最后,[玛丽亚娜]相信婚姻制度是伟大与救赎的障碍:难道这不是天主教神父不允许结婚,以及沉思修道院成员最接近上帝的原因吗?”(西斯马鲁,1986 年,第 1353-1354 页)。“对他来说,新世界没有财富,对她来说,没有婚姻和幸福!这是一种彻底的拒绝,受一种对纯洁的虐恋式浪漫主义的驱使……这位主人……不是基督教模范的榜样,因为他的自私、残忍以及他所有的行为都带有可怕的不人道性……阿尔瓦罗的爱是一种消灭的爱;他有一种冷酷,只有他的骄傲才能解释……”(勒姆利,1967 年,第 345-346 页)。
“即使在他最好的时候,[阿尔瓦罗]也只是一个半基督徒……因为他所必须应用的基督教是不完整的……他强烈地感受到基督教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即它超凡脱俗,它蔑视尘世的舒适和财富,它放弃了世俗的东西,但他对它所赋予的与上帝合一的意识却一无所知……现在,阿尔瓦罗的宗教几乎完全……在于对上帝的无限伟大与距离的意识……但化身呢?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温柔结合呢?……这些事情仍然超出了阿尔瓦罗的体验……真正基督教的性格……是……玛丽亚娜,她最终牺牲了自己,以便与他一起放弃世俗”(霍布森,1953 年,第 179-181 页)。
“对许多人来说,蒙泰朗的‘基督教’戏剧似乎是对狂热的探索,缺乏圣洁的品质,这种狂热远远没有达到神圣的程度,充其量只是对自我的狭隘超越……唐·阿尔瓦罗表达了一种愿望,即把自己从所有世俗的商业和关注中隔离出来,进入一个精心策划的孤立状态,以进行沉思,并获得救赎……世界对他来说太过分了,他不理解它,而且他不再想要理解它……玛丽亚娜被描绘成一个永远站在她父亲和上帝之间的障碍。她的父亲对通过允许她结婚来保证玛丽亚娜的幸福没有兴趣……家庭制度被谴责……骑士团是拥有共同信仰和高贵理念的选民精神的真正家庭。它不会强加附件……玛丽亚娜严肃地声明她不希望幸福,这为她最终与父亲的理解做好了准备……父亲用斗篷盖住自己的双肩和女儿的双肩,这是一个象征他们狂喜和遗忘——或者他们的疯狂和他们对生命的放弃——的姿态”(约翰逊,1968 年,第 110-113 页)。
"圣地亚哥之主"
[edit | edit sourc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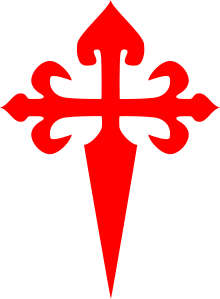
时间:1519 年。地点:西班牙阿维拉。
文本在?
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成员在他们的团长唐·阿尔维罗的家中集会。其中三位成员决定在新世界碰碰运气。对于阿尔维罗来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腐败不堪,无法与西班牙人在格拉纳达战役中赶走摩尔人时那个辉煌的时代相比,那时他“在战争的披风中凝视着上帝”。将印第安人改宗的表面目的不过是“不洁和排泄物”,因为对金钱的渴望,没有将印第安人送往天堂,却将西班牙人送往地狱。当他的朋友们离开后,阿尔维罗独自一人感到欣慰。“哦,我的灵魂,你还在吗?”他自言自语道,“哦,我的灵魂,终于只有你和我了!”一位朋友,唐·贝尔纳尔,听说他的儿子雅辛托和阿尔维罗的女儿玛丽安娜之间有婚约。由于雅辛托的挥霍无度,贝尔纳尔建议他和其他人在新世界发财,这个计划立即遭到团长的坚决拒绝。阿尔维罗对金钱毫无兴趣,即使是为了他世界上最爱的女儿。 “你不会偷走我的贫穷,”他警告他的朋友。他严厉地指责女儿在这件事上的不诚实,称爱情是“猴子戏”。“女儿的父亲还是父亲吗?”他反问自己。为了帮助这对年轻恋人,贝尔纳尔请求索里亚伯爵误导阿尔维罗,让他以为国王命令阿尔维罗以管理者的身份前往新世界,但玛丽安娜无法欺骗父亲,她向父亲坦白了真相,破坏了计划。厌倦了世俗事务,阿尔维罗前往圣巴拿巴修道院,那里也是玛丽安娜可以居住的地方。她接受了提议。他用圣地亚哥骑士团的白袍覆盖着她,外面的雪正在下,父女俩似乎准备被埋葬在神秘的雪中。
安德烈·纪德
[edit | edit source]
另一部以宗教为主题,但更具批判性的戏剧是安德烈·纪德(1869-1951)创作的《梵蒂冈地窖》(The Vatican cellars,1950),该剧改编自他 1914 年的同名小说。该故事源于 1893 年的一个历史事件(爱尔兰,1970 年 p 252),“一位狡猾的律师、一位被逐出教门的修女和一位有争议的牧师在里昂合谋散布谣言,说利奥十三世被共济会枢机主教囚禁,并被一个假教皇取代,他们从信徒那里收取赎金以释放教皇”(画家,1968 年 p 67)。以下评论针对的是小说,但也同样适用于戏剧。
“有两个主要情节……拉夫卡迪奥的故事和阴谋的故事……由家庭关系联系在一起……[梵蒂冈骗子的目标]……是要愚弄社会”(画家,1968 年 pp 66-67)。“地球上的教皇,根据定义,应该是无误真理的宝库,由神明保证。但当然,教皇的真实性也需要得到保证:只有在你能毫无疑问地确定你面对的是唯一的无误教皇时,你才能相信教皇言论的无误性”(爱尔兰,1970 年 p 270)。
“普罗托斯将人类分为两种类型:‘微妙的’,普罗托斯当然属于这一类,他们是那些受变形能力的影响而对任何特定情况做出灵活多变的反应的人,这些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会在所有人和所有场合都展现出相同的姿态;他们是‘甲壳动物’的敌人,他们是僵硬的、孤立的、原则性强的人……普罗托斯……接受所有贵族和资产阶级甲壳动物……是逃避的化身——逃避社会……自我……过去,以最野性的纪德式意义上的逃避,以及创造性精神的持久流动不安的意义……朱利叶斯……是一位小说家,他的失败源于他性格的过度逻辑性……拉夫卡迪奥[是] 躁动不安的、放荡不羁的[但]他给自己强加了严格的自我控制纪律……甚至为了最轻微的自我克制失误而用刀笔自虐”(托马斯,1959 年 pp 157-161)。“拉夫卡迪奥,一个年轻的流浪汉……既美丽又无道德”(波拉德,1991 年 p 365)。拉夫卡迪奥的“天生的优雅和优越成就使他在社会下层阶层格格不入,而他的出身和身份的谦卑又排除了他进入上层社会”(爱尔兰,1970 年 p 262)。每个甲壳动物,朱利叶斯、安提梅和阿玛迪乌斯,“都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和习惯,从自己所有的过去中根除自己”,但由于他们是甲壳动物,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奥布莱恩,1953 年 p 180)。
人们对拉夫卡迪奥谋杀的动机提出了不同的,但部分重叠的观点,这似乎是一个毫无必要的行为。作为一个私生子,拉夫卡迪奥“无意识地渴望被认可和得到父爱——他是否拥有它们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他已经无法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已经变成了同样无意识的复仇需求。在弗勒里索瓦尔平庸的资产阶级形象中,他推翻了拒绝他的社会”(画家,1968 年 p 72)。“在赶走阿玛迪乌斯时,拉夫卡迪奥不仅在反抗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家庭和所有坚硬甲壳动物的统治制度,而且也在反抗瓦格纳和帕西法尔,以及所有崇拜他们的人……拉夫卡迪奥是一个爱玩感觉和情绪的暴躁赌徒”(奥布莱恩,1953 年 pp 185-186)。他是一个自恋狂,“渴望自我认知……源于一种疯狂的急切麻木,一种对最强烈的感觉的贪婪欲望”(托马斯,1959 年 p 162)。“对他的同伴感到厌倦和好奇,拉夫卡迪奥让自己的想象力漫游……正是[这种]明显的缺乏动机才构成了命题的兴趣所在……他好奇的是他自己”(爱尔兰,1970 年 p 263)。
"梵蒂冈地窖"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 世纪 90 年代。地点:意大利。
文本在?
安提莫斯是一位无神论者,也是一位残疾人,他对他妻子维罗妮卡感到愤怒,因为维罗妮卡向圣母玛利亚献上了祈求他恢复健康的蜡烛。令他惊讶的是,在黑暗中独自一人,他听到了圣母的声音,并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高兴地扔掉了拐杖,并皈依了天主教信仰。安提莫斯的富有的姐夫朱利叶斯是一位作家,他的垂死的父亲,一位伯爵,要求他去看望父亲的私生子,一个名叫拉夫卡迪奥的年轻人,他从未见过。为了获得拉夫卡迪奥的信息,朱利叶斯给他提供了一些秘书的工作。在他父亲的遗嘱中,他将一大笔钱留给了拉夫卡迪奥,前提是拉夫卡迪奥承诺不再用自己的身份打扰家族的其他成员,因此他不需要接受朱利叶斯提供的工作。在去朱利叶斯家的路上,拉夫卡迪奥从一栋着火的房子里救了两个孩子,赢得了朱利叶斯女儿詹妮弗的赞赏。拉夫卡迪奥向朱利叶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被伯爵去世的消息打断了。与此同时,朱利叶斯的另一个姐夫阿玛迪乌斯听到一个谣言,说教皇利奥十三世被绑架,并被关押在圣安吉洛堡垒的地下室里,该堡垒与梵蒂冈相连,而一个冒牌货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个谣言是假的,是由拉夫卡迪奥的校友普罗托斯散布的,目的是为了从愚蠢的天主教徒那里骗取大量的钱,以释放教皇。当阿玛迪乌斯到达罗马时,普罗托斯伪装成牧师,与他交朋友,并带他去那不勒斯,去看望他的同伙巴多莱蒂,后者假装成枢机主教,要求他将 6000 法郎的债券兑换成现金。与此同时,朱利叶斯也来到罗马,向教皇请求赔偿安提莫斯损失的收入,因为安提莫斯不再受到他曾经在职业生涯中依靠的共济会的保护。然而,他的任务没有成功。阿玛迪乌斯向他透露了他知道的关于失踪教皇的事情,但朱利叶斯很难相信这样的故事。尽管如此,他还是帮助阿玛迪乌斯从银行取回了钱,并给了他一张以他名义的车票。巧合的是,当阿玛迪乌斯从罗马乘坐火车前往那不勒斯时,他遇到了拉夫卡迪奥,两人互不相识。拉夫卡迪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倦,但他愿意将命运推向极点,于是将他从车门扔了出去,导致他丧生。他带走了阿玛迪乌斯的车票,但没有带走 6000 法郎。在罗马与朱利叶斯见面时,拉夫卡迪奥惊讶地发现,被杀的人是朱利叶斯的姐夫。为了嘲弄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在桌子上留下了阿玛迪乌斯的车票。朱利叶斯发现后,非常担心自己会成为这个未知凶手的下一个受害者。拉夫卡迪奥不知道的是,他的谋杀被普罗托斯看到了,普罗托斯建议他的老朋友,他们可以以此来勒索朱利叶斯。拉夫卡迪奥拒绝了,并将自己的罪行告诉了朱利叶斯,詹妮弗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场谋杀让詹妮弗更加爱上了这个男人。拉夫卡迪奥带着她逃跑了,最后说:“我们会一起找到自救的办法。”
雅克·奥迪贝尔蒂
[edit | edit source]
一座桥梁连接了雅里的《尤利西斯王》(1888)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以及 50 年代的荒诞剧。达达主义戏剧的一个例子是特里斯坦·查拉的《煤气心脏》(The gas heart,1921),该剧以荒诞无稽为主。超现实主义戏剧的例子包括罗杰·维特拉克的《维克多,或孩子们掌权》(Victor, or the children come to power,1928)和《爱的奥秘》(The mysteries of love,1927)。这两个运动的剧作家都试图用梦境般的意象推翻中产阶级的习俗。超现实主义者表现出对用新社会取代主流习俗的兴趣,包括共产主义社会,而达达主义者则很少愿意用任何东西来取代它们。一座桥梁还连接了存在主义戏剧和雅克·奥迪贝尔蒂(1899-1965)的《恶贯满盈》(Le mal court,1947),该剧也表现出与过去的亲缘关系,包括格奥尔格·毕希纳的《莱昂斯与莱娜》(Leonce and Lena,1836)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幻想曲》(Fantasio,1834)。
在《邪恶蔓延》中,“情节和主题故意采用传统手法,笼罩着童话般的神奇光芒。角色大多拥有功能性名字……并且缺乏心理上的实质。他们倾向于用抽象的术语交谈……但他们的虚构世界从未受到来自外部的怀疑或问题的困扰”(Bradby,1991年,第188页)。“情节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为了说明主题,即邪恶的无所不在和不可阻挡的力量。奥迪贝尔蒂使用了一个传统的童话情节:美丽的年轻公主,一位贫困国王的女儿,要去嫁给一位富有的年轻国王;邪恶的红衣主教出于政治原因干预并阻止了婚姻;美丽的年轻公主心碎,等等……奥迪贝尔蒂只将他的经典童话公式推进到一定程度:富有的年轻国王并没有将邪恶的红衣主教扔进地牢,以便他最终能娶到美丽的年轻公主。相反,公主,阿拉丽卡,随着剧情的推进,发现自己一直被邪恶和欺骗所包围。她对美好生活以及人们的善良和可信的幻想,在痛苦的震动中,一个个地从她身上脱落。她发现,她计划中的婚姻很久以前就被秘密放弃了,她被当作诱饵,以便年轻国王可以与政治上更有利的人结婚。甚至她年迈忠诚的保姆也参与了阴谋。她绝对没有人可以信任。每个人都自私、腐败、不诚实,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虚假和腐败的社会中,并按照这个社会的规则生活。随着她不得不经历的一系列冲击把她打入对世界真实本质的认识,阿拉丽卡意识到,如果她想作为棋子以外的人生存下去,她就必须与之妥协。她决心用邪恶对抗邪恶——让“邪恶蔓延”。她废除了她友善、笨拙的年迈父亲,无视他对她孝敬的恳求,并决心以彻底的冷酷统治。如果一切都邪恶,那么最邪恶的人就会获胜”(Wellwarth,1962年,第336页)。
《邪恶蔓延》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40年代。地点:虚构国家肖特兰。
文本在?
阿拉丽卡,肖特兰的公主,必须出于政治原因嫁给奥西丹特的国王帕菲特。她听到有人敲门,一个声音说国王已经到了。在公主和所谓的国王交谈时,她的副官发现这个人是冒牌货。当入侵者费迪南德试图离开时,副官向他开枪,但让他活了下来。当阿拉丽卡和她的女管家讨论此事时,又听到有人敲门,再次说国王已经到了。这次是真正的国王,他发现公主很吸引人,但与他同行的红衣主教透露,他们的婚姻前景已被取消,因为国王娶西班牙国王的女儿更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将与西班牙结婚,让她怀孕,”红衣主教肯定地说。然而,在他离开期间,国王向阿拉丽卡求婚,并得到了她的接受。他们出发前往奥西丹特,但当谈到如何处置费迪南德时,阿拉丽卡建议让他与他们同床共枕。国王对这个建议感到震惊,不再知道自己会怎样。虽然阿拉丽卡和费迪南德睡在同一张床上,但他们发现很难达成一致。“你应得的只是让我把你像梳子在汤里一样,在你的想法中游荡,”他说。与此同时,肖特兰国王塞莱斯廷辛克要求知道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他女儿的卧室里。她越来越奇怪,以至于塞莱斯廷辛克怀疑他的女儿疯了。“邪恶蔓延。一只雪貂!一只雪貂!无论如何都要让它蔓延,”她说。塞莱斯廷辛克下令逮捕费迪南德。阿拉丽卡不同意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她的生活只是为了“掩盖我凶猛的当前龙卷风,”她说。在阿拉丽卡的启发下,费迪南德提议在肖特兰土地上进行重大改进,令元帅感到震惊,他发现他的计划“完全惊人”。阿拉丽卡提议副官和元帅放弃对他们父亲的忠诚,完全服从她和她的丈夫,成为肖特兰的女王和国王。他们同意。“邪恶蔓延,”阿拉丽卡高兴地总结道。
阿图尔·阿达莫夫
[edit | edit source]
阿图尔·阿达莫夫(1908-1970)是另一位超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的成名之作尤其在于在《入侵》中呈现了作家的困境(《入侵》,1950年)。
“至少我们可以说,皮埃尔的生平,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其他人的生平,都被让的难以解读的遗产所入侵。然而,一个真正的问题是,让是否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手稿视为一种象征,象征着不可辨认的意义,这种意义从本质上入侵了生命……因此,皮埃尔成为了一种现代人的典型,他陷入试图发现生命的意义的任务中,而生命的意义仍然模糊不清,同时,他又无法放弃这种斗争。皮埃尔的策略是放弃一切集体努力,独自追求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因此,他的个人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宗教探索的特征,这种宗教探索是在隐居中进行的。当他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他拒绝与任何人交谈。他的母亲用托盘送来食物,但没有和他交谈……艾格尼丝的存在总是代表着更新的可能性。在第一幕中,她是使用打字机的人,一种交流工具。当她在身边时,房间很凌乱,但感觉是在混乱中存在着创造性的可能性。然而,随着皮埃尔越来越从他与艾格尼丝的关系中抽离,这些可能性减少了。然后,当皮埃尔退缩到孤独中时,艾格尼丝的性意义转移到第一个出现的人身上,艾格尼丝就和她的新情人离开了。我们从她回来拿打字机时得知,第一个出现的人病倒了,她只能努力维持他的生意。因此,也许,瓦解和更新都体现在她身上,但就她与皮埃尔的關係而言,更新仍然是一种可能性。当皮埃尔在最后对他的母亲评论说,如果艾格尼丝有更多的耐心,他们两个人就能在手稿上开创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四月式的更新的话,这种可能性就被强调了。但这种可能性最终被母亲挫败了,皮埃尔的命运被封印了”(Sherrell,1965年,第401-403页)。
“皮埃尔、艾格尼丝和他们的朋友兼合作者特拉德尔,他们之间意见不一致,无法实现集体的重新单一化,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抵抗母亲及其同伙的入侵……母亲是一个入侵者。她在她儿子的公寓里住了下来,逐渐将自己对秩序的标准强加于此……房间整洁有序,移民也被阻止了。随着场景的推进,皮埃尔消失在他的房间里,独自一人死去。他是否自杀尚不清楚,但通过鼓励艾格尼丝离开,然后阻止她回来,母亲无疑促成了他的死亡……皮埃尔、艾格尼丝和特拉德尔无法联系起来,制定出抵抗保守势力的策略,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利益。观众可以看到母亲的权力攫取,但那些将受到这种权力攫取最严重伤害的人却看不到”(Chamberlain,2015年,第154-155页)。
“死者的文件对皮埃尔来说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对意义的探索,尽管在整部戏剧中都有讽刺性的暗示,表明让的遗产可能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艾格尼丝本人似乎代表着混乱;毕竟,正是通过她,皮埃尔才与她的兄弟及其文件有了牵连……《入侵》对工作的有效性以及爱和友谊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阿达莫夫似乎在说,这就是所有人类努力的最终结果:徒劳”(Parsell,1986a年,第15页)。
“《入侵》强调了真理的相对性,在一个绝对真理无法获得的世界中,标题指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入侵了已故作者的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这些人费力地试图破译笔迹,澄清作品,最终以一种令人沮丧的僵局告终,因为除了他们自己之间意见不一致外,他们还对每一个词都有不同的解读,直到没有人能确定真正的含义”(Bishop,1997年,第56页)。
“关于某些关键段落的转录和含义存在着广泛的分歧。皮埃尔努力整理他朋友的作品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妻子、朋友,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皮埃尔的危机发生在他不再能感受到语言的活力之时……当他说语言失去了空间存在的性质时,他的意思是思维不再可能,因此他的存在本身也危在旦夕”(Bradby,1991年,第83-84页)。
《入侵》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50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在?
彼得努力破译妻子艾格尼丝已故兄弟留下的手稿。他慢慢地整理着这些文本,艾格尼丝则负责打字。他们的朋友特拉德尔也提供了帮助,但这两个男人在处理方法上意见不合。彼得认为应该获得最准确的逐字逐句版本,而特拉德尔则认为应该获得一个近似的版本,通过他们对文本含义的直觉理解来完成。由于分歧,彼得独自工作,尽管特拉德尔警告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已故朋友的家人正在寻求法律途径获得这些文件以供自己使用。彼得认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一个陌生人出现,要买下隔壁的公寓。这个陌生人对看起来很悲伤的艾格尼丝心生怜悯,而她却几乎完全被专心致志的丈夫忽视了。彼得无法继续他的工作,决定暂时放弃,住在他们公寓里一间僻静的房间里,免受任何打扰。“只要事情没有呈现出一定的视角,我就无法得到安宁,”他断言。艾格尼丝和特拉德尔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彼得的母亲像往常一样给他送饭,但他警告她不要对他说话。当彼得躲进小房间后,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向艾格尼丝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他们一起离开了,令彼得的母亲忍俊不禁,她笑着拍着大腿。当彼得从房间里出来时,他准备过上普通的生活。他撕毁了那些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的纸张,然后得知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表示理解她的决定,考虑到他们在一起的混乱生活,但他的母亲责怪她是混乱的根源。当他离开房间时,特拉德尔回来,透露艾格尼丝的家人准备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文件,但发现所有文件都被撕毁了。出乎意料的是,艾格尼丝回来了,但只是暂时,因为她的朋友病了。短暂的交谈后,母亲把她推了出去。当特拉德尔寻找彼得时,他发现他已经死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他说道。母亲对这件事感到震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让·热内
[edit | edit source]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主要剧作家是让·热内(1910-1986),他的代表作有《女仆》(Les bonnes,1947)和《黑人》(Les nègres,1958)。
“《女仆》的开场是当代戏剧中最精彩的场景之一。完全摒弃了铺垫,它将我们直接带入到我们最终会理解为两个女仆姐妹定期进行的仪式中。观众最初会被女主人和她的女仆的怪异行为所迷惑,但他们会发现一种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风格化的支配游戏……姐妹们每天进行的结构化的幻想之旅是她们在令人窒息的现实中生存的方式。她们对“夫人”的舞台化反抗使她们不必反抗真正的“夫人”……事实上,当我们在剧中看到真正的“夫人”时,她显然不是仪式中描绘的暴君,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女仆们的看法。她们反抗的需要是真实的,但她们反抗的愿望被她们对“夫人”的迷恋所破坏。因此,她们满足于模拟反抗,这种反抗既针对彼此也针对“夫人”,是一种刻意限制的风格化表演,旨在仅止于谋杀之前”(Bishop,1997年,第125-127页)。从《女仆》一开始,索朗日就扮演着她的女主人“专横和侮辱”的角色……女仆们对夫人的反应是矛盾的,混合着仇恨和爱,嫉妒和崇拜,其中仇恨和嫉妒占主导地位……“女仆”中的戏剧冲突是仆役地位或角色与夫人地位之间的冲突”(Jacobsen and Mueller,1976年,第138-143页)。“这两个女仆之间存在着相互憎恨的纽带,她们是彼此的镜像……同时,在夫人的角色中,克莱尔将所有仆役视为上层阶级的扭曲镜像。因此,她们在彼此身上憎恨的反射,是她们崇拜、模仿和憎恨的,安全的主人们世界的扭曲反射”(Esslin,1974年,第174页)。“戏剧对话一开始显得奇怪地漫无目的——她们似乎只是在谈论自己、她们的处境以及她们想要改变的方式——但观众逐渐开始理解她们讨论背后的戏剧驱动力:她们试图说服自己进入一种转变状态,在那里她们可以逃脱她们受限的存在,成为她们不是的东西:自由主体。因为在热内的戏剧中,表现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表现世界本来面目,而是为了表现我们通过想象力构建的我们自己和塑造那些想象中的自我的力量的夸大和扭曲……女仆们反复宣称她们对夫人的忠诚,可以被看作是她们渴望分享夫人所拥有的存在,而不是简单的爱情表达。她们痛苦地意识到夫人是如何恩赐她们,如何仅按照她的心情变化对待她们,而没有考虑她们的感受,但她们仍然认为,与她们相比,夫人的存在非常令人向往”(Bradby and Finburgh,2012年,第35-36页)。“因为她们如此憎恨自己的位置,她们也憎恨彼此和自己。正如索朗日所说,“污垢不喜欢污垢”。仆人们因为这种憎恨而失败了。正如马尔罗和萨特提到的,“革命只有在受压迫者能够将自己的现状视为未来尊严的潜在来源时才有可能”……索朗日和克莱尔没有其他价值观可以提供……她们想拥有夫人的品质,虽然她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愤怒可能会在谋杀的梦境中表达出来,但最终她们只是惩罚了自己”(Thody,1968年,第165-167页)。“当夫人出现时,她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可怕人物,而是一个相当普通、富有、过于浪漫、肤浅的世俗女人……克莱尔现在意识到,她们对夫人的第一次行动必须是杀死她们自己内心的那些她们如此憎恨的夫人元素——她虚伪的优越感和她的自以为是……索朗日的最后一段话是第一次诚实而平静的”(Gascoigne,1970年,第191页)。Henning(1980年)认为,“当夫人回来时,循环似乎已经完成。但这同样只是幻象。雇主自己并不是她最初看起来的那样真正的资产阶级夫人,也不是真正为她所爱的男人而受苦的忠诚女人。她也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她的行为甚至像是女仆们开场仪式动作的模仿。她自己只是另一个替代君主……克莱尔确实表现出她们夫人的行为,但在女仆们的私人仪式中,是索朗日,而不是夫人,扮演着仆人的角色。因此,角色的仪式逆转只实现了一部分,仆人们只能贬低自己”(第80-81页)。“女仆们穿着制服和夫人的衣服,在多个方面具有双重身份:受辱的苦工和胜利的复仇者,囚犯和想象中的旅行者,创造者和厨房炉灶的奴隶,她们还添加了另一种形式的二元性,即孩子和成年人……当克莱尔穿上夫人的衣服时,必须用别针别起来,因为她太小了,无法穿下成年人的衣服。克莱尔和索朗日可能没有长大,这一点可以从她们睡在折叠床上得到进一步证明。虽然她们把自己的生活献给了复仇,但她们在房间里以虔诚的孩子的方式背诵祈祷文。她们用护身符装饰阁楼,包括夫人的花束,这表明孩子拒绝放弃任何财产”(Hubert,1969年,第204-205页)。“女仆们模仿夫人,因为她们渴望被融入社会贵族阶层……克莱尔和索朗日除了与夫人之间的关系之外,没有自己的身份;因此,她们想拥有唯一定义她们存在的人……夫人美丽、善良、富有,是男人的磁石;女仆们丑陋、恶毒、贫困,没有男性朋友。克莱尔和索朗日因无法改变她们的社会或经济地位而感到沮丧,因此嫉妒并因此鄙视夫人,她对仆人的恩赐态度只会加剧她们的复仇欲望。女仆们憎恨屈服,感到无法诚实地与她们的“保护者”说话,并且在夫人周围越来越受到性压抑,夫人的本质是由她的性能力定义的。克莱尔和索朗日参与了一种仪式化的仪式,旨在摧毁“夫人”的精神,以便这些被排斥的人……可以超越她们低下的地位,蔑视已建立的统治阶级”(Plunka,1992年,第176-177页)。“夫人当然是被包养的女人,因此与女仆们本身有着奇特的关系。她实际上是另一个次世界的成员,当然比女仆们更高的次世界,但无论如何都是次世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她也依靠幻想和想象生活。我们立即从她戏剧化地描述了先生被捕的方式中看到了这一点。她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被疏远了,就像女仆们一样。我们还进一步看到,她在与先生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两个女仆角色的原型。她现在讲述了关于他被捕的故事,匿名信以及她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英勇角色。索朗日试图安慰她。她说先生是无辜的,将会被无罪释放。“他是,他是,”夫人回答。然而,一个错误的音符出现了。我们了解到夫人很享受她作为殉道者和圣徒的角色。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忠于先生。她会从一个监狱追随他到另一个监狱。她会放弃她优雅的生活,她的香奈儿定制的漂亮衣服,她的皮草。她甚至对她的两个仆人表现出虚假的同情。她们会一起退休到乡下。她们会忠于她,她会照顾她们”(Pucciani,1963年,第53页)。“这部非凡的戏剧,它拥有完美的单幕结构,压倒性的戏剧张力,以及思想和象征的密度,被公认为当代戏剧的杰作之一。这是一部关于面具和双重的戏剧,关于身份的虚无缥缈”(Coe,1986b年,第682-683页)。
“黑人”这个词是对白人对黑皮肤人民的看法、言论以及他们因偷偷摸摸的内疚和压抑的厌恶而无法说出口的蔑视的讽刺和嘲弄。这一切都带着一丝微笑,这微笑缺乏幽默感,但会激起人们的恐惧的笑声”(克鲁尔曼,1966 年,第 74-75 页)。“拒绝了普遍的爱这一‘白色’价值观,仪式参与者必须努力发现绝对的仇恨。仪式核心是 Village 对白人女性的谋杀重演。舞台中央摆放的灵柩据说是她的尸体,并且关于 Village 是否被她吸引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对负责仪式的 Archibald 很重要,因为他必须确定这是否是一起出于纯粹的仇恨而犯下的罪行:‘他的罪过救了他。’” (Bradby 和 Finburgh,2012 年,第 75 页)。“主要的问题是……Village 是否出于正确的动机和精神犯下了谋杀。他的行为是否以一种能充分体现黑人灵魂的方式执行?……因此,Village 就有必要重演谋杀……Archibald 提醒他们目标:‘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谴责,让他们做出判决,让我们受到谴责’……他们必须符合白人定义的黑人概念。但是,[之后] 黑人已经走向……他们自己行为的决定者……法官……震惊于没有发生谋杀,看到了自己角色的消失……被附身者……必须止步于谋杀……因为[那] 会剥夺[他们]的占有”,因此角色发生了逆转(Jacobsen 和 Mueller,1976 年,第 158-162 页)。“在彼此的关系中,Village 和 Virtue 无力为力;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黑人身份是否定,仅仅是白人的一种功能。它自我实现的唯一机会是颠倒图像和倒影的角色。只有通过摧毁、征服、统治或吸收白人,通过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来对抗征服者的价值观,黑人才会成为图像,而白人则会沦为镜中之像”(Coe,1968 年,第 292 页)。舞台事件与幕后起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为观众上演的戏剧是一种欺骗,掩盖了舞台上黑人的真正动机:一种仪式性的自我毁灭和随后对白人价值观的驱除,产生了一种通往新身份的过渡仪式……观众席上的白人很乐意看到黑人模仿白人文化……黑人与 19 世纪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野蛮原始世界的看法相关联……法庭,由戴着白色面具的黑人扮演,代表着白人社会,或者至少是黑人对白人社会的刻板印象……黑人剥夺了白人权威和力量,建立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体现在幕后对一名黑人叛徒的审判中……Diouf,以 Marie 的身份,生下了五个代表着白人法庭的玩偶……[象征着] 白人种族的灭亡”(Plunka,1992 年,第 226-233 页)。“仪式的目的是瓦解白人形象,起义的目的是瓦解白人”(Brustein,1964 年,第 408 页)。“在 Genet 的戏剧中,所有白人都是制服的,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事实上,他们是权威的象征。在殖民地非洲,当地秘密社团和社交俱乐部经常为他们的官员提供女王、总督、法官和传教士的服装和头衔,因此既模仿了白人,又挑战了他们对权威象征的垄断”(Graham-White,1970 年,第 210-211 页)。“法庭由戴着白色面具的黑人组成。这些戴着面具的人暗地里渴望颠倒事物的秩序,成为压迫者,成为权威的声音。但他们很清楚自己属于黑人无特权种族……白人法庭的成员想要履行他们的义务,这表明他们对未来抱有一定的信心;然而,他们不想以白人的身份履行他们的职责,而是以黑人的身份”(Knapp,1968 年,第 137 页)。“这出戏中的法庭是无效的。必须由黑人审判他们中的一员。白人法庭无效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他们的讲话充满了随机的爆发,导致审判无果而终。对这一点的解读可以是白人法庭无法理解和解释黑人罪行……另一种解读可以是……正义对黑人来说是不可能的”(Bennett,2011 年,第 82 页)。“摧毁白人形象被认为是改善他们状况的唯一途径。黑人在获得政治独立、能够享受除了仇恨之外的其他情感的目标上与白人作斗争”(Thody,1979 年,第 199 页)。“‘黑人’首先以莫扎特的旋律跳着小步舞曲围绕着一个灵柩,灵柩占据舞台中央。虽然他们的动作中明显带有模仿的元素,但小步舞曲象征着黑人对白人文化的奴役。这种奴役是这出戏的起点和终点”(Oxenhandler,1975 年,第 422 页)。“演员分成两组出场……但最终的舞台形象是团结一致的:‘所有黑人——包括那些曾经是法庭的人,现在没有面具——站在一个用白色覆盖的棺材周围……白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被嘲笑、贬低,并沦为‘演奏查尔斯·古诺的曲子’、编织‘给烟囱扫烟的人用的毛线帽’、在‘风琴上唱歌’和在星期天祈祷……演员正在为 Diouf(伪装成白人受害者)的‘谋杀’而激动起来,这时 Village 停止了行动。到目前为止,Village 一直努力地用反复出现的旁白向观众解释他的行为,但现在整个仪式将超出观众的理解范围,因为叙述让位于魔法……在 Diouf 的叙述中,法庭与仪式中的演员融为一体。他们为模仿的动作鼓掌和欢笑,就好像它们是真的。与此同时,被困在舞台上的白人观众,他的手被编织的毛线帽绑着,可以说,除了看着之外,无能为力……这出戏的行动不是为了解决最初情境的冲突;相反,它倾向于加剧它们”(Webb,1969 年,第 455-458 页)。“传教士……自豪地宣称,白人信徒默许,黑人信徒则感到困惑地拒绝,上帝是白色的,这个信念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来阻止敬畏上帝的黑人寻求爬上平等阶梯的顶峰。‘两千年来,上帝一直是白色的。他用白色的桌布吃饭。他用白色的餐巾擦拭白色的嘴。他用白色的叉子挑着白色的肉。’黑人意识到,他们最终的精神解放只有在他们能够拒绝和修改白人使用的颜色符号之后才能实现。因此,Felicite 在这出戏的最后说道:‘一切都改变了。任何温柔、善良、美好和温柔的东西都将是黑色的。牛奶将是黑色的,糖、米饭、天空、鸽子、希望都将是黑色的’……这出戏中的黑人从强调社会反对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从一开始,黑人就进行着一种黑人美丽的仪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他们的黑人身份,如果他们表现出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斥责。Archibald,他一直在推动剧情发展……建议 Neige:‘你想变得更有吸引力——还剩下一些黑粉’”(Warner,2014 年,第 201-203 页)。“整部戏都是一首仇恨的赞歌:黑人对白人的憎恨被故意地渲染和赞美……灵柩在整部戏中都以视觉形式占据舞台中央。因此,正是所有种族主义恐惧中最深刻的一种,即种族间性嫉妒,被 Genet 利用”(Martin,1975 年,第 519-522 页)。“无论他的白人观众对黑人在做什么持多少反对意见,他们并不是为了邪恶本身而寻求邪恶,而是为了可以理性地表达的政治目标:独立、自由、自尊”(Thody,1968 年,第 200 页)。
Antonin Artaud 预示了 Genet 的戏剧在创造神话的目标、将语言用作咒语、传达情感而不是交换思想、以及使用“音乐、舞蹈、造型艺术、哑剧、模仿、手势、语调、建筑、布景和灯光”等形式的视觉和听觉辅助方面的先见之明 (Artaud, 1938)。“Genet 从一个完全解放的潜意识的深处汲取了他的神话,在那里,道德、抑制、优雅和良知没有任何影响;他的作品的基础是 Artaud 认为是所有伟大神话根源的黑暗性自由”(Brustein,1964 年,第页)。“Genet 的所有戏剧都向我们展现了反社会。监狱、妓院、黑人或叛乱者的世界都是通过反对传统、习惯、正确思考的社会来定义的。生活在这些世界中的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意识本身都是由他人的蔑视所决定的。但 Genet 的戏剧并没有像一些荒诞剧那样,在一个噩梦般的恐怖景象中消解所有社会差异。相反,他们精确地考察了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层次,他们展现了变形仪式,在这些仪式中,被压迫者通过接受和夸大自己的处境,希望将耻辱转变为自豪,改变游戏的规则,从而扭转压迫者的局面”(Bradby, 1991 年,第 179 页)。
"女仆们"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40 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位于 https://web.mit.edu/jscheib/Public/phf/themaids.pdf https://pdfcoffee.com/genet-jean-the-maids-amp-deathwatch-grove-1954pdf-2-pdf-free.html
克莱尔命令她的女仆索朗日,让她穿上所有的华服。她不断地指责激怒了索朗日,让她怒火中烧。她打了克莱尔,并威胁要做出更糟糕的事情,直到闹钟响起,克莱尔才喊到:“快走吧,夫人要回来了。”克莱尔也是一名女仆,她们只是在玩角色扮演游戏。克莱尔责怪她姐姐总是迟到,因此她们永远无法到达杀害主人的时刻。尽管她们在奴隶状态中存在着固有的挫折,但克莱尔仍然认为,在内心深处,他们的女主人爱着她们。“是的,”索朗日讽刺地评论道,“就像她厕所里的粉色珐琅一样。”为了报复她们在角色扮演之外的命运,克莱尔给警察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她主人的情人抢劫,导致他被捕。索朗日打算走得更远,透露她曾经在主人睡觉时动过杀她的念头,但她行动时却胆怯了。“她会用她的温柔腐蚀我们,”她警告道。令她们沮丧的是,克莱尔从电话中得知那个人被保释了。克莱尔更加责怪她姐姐没有杀掉她。现在,她们很有可能被指控为诬告而入狱。“我已经受够了做蜘蛛、伞柄、肮脏无神的无家可归的修女,”克莱尔沮丧地说。她们又编造了更多针对她们主人的指控,但毫无实际作用。“可是我们不能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杀了她,”索朗日承认道。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建议在她们主人的菩提花茶中溶解巴比妥类药物。她们的主人走了进来,为她情人的处境而感到难过,准备追随他到遥远的监狱。“我会拥有更新更漂亮的衣服,”她决定道。她给了克莱尔她的丝绸长裙,给了索朗日她的毛皮大衣。然后,她注意到电话没有挂断。索朗日脱口而出,说她的情人打电话了。她被引导着透露,她的女主人将在一家餐厅与他见面。女主人想要立刻加入他,在喝下毒茶之前就离开了。“所有的阴谋都无济于事。我们完蛋了,”克莱尔总结道。索朗日建议她们逃跑,但克莱尔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因为她们都很穷,无处可去。她们毫无用处地诅咒着她们的奴隶身份。在绝望中,她们又开始玩角色扮演游戏,这次是索朗日扮演女主人,要求她的茶。但克莱尔又重新扮演了女主人,吞下了毒茶,而索朗日的手交叉在一起,仿佛已经被手铐铐住。

时间:1950年代。地点:白人殖民统治的非洲。
文本在?
一群黑人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白人女性被谋杀的场景,观众是另一群伪装成白人的黑人,包括女王、总督、法官、传教士和一个仆人。阿奇博尔德·阿布萨隆·韦灵顿是仪式主持人,引导着表演的精神,对白人殖民统治的仇恨越来越深。在灵车前,阿奇博尔德问村民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村民回答说他亲手勒死了名叫玛丽的白人女性。听到这个消息,女王悲痛欲绝。“放心,陛下,上帝是白人,”传教士安慰她说。当一些黑人分心,无法为任何有价值的事业做出贡献时,阿奇博尔德提醒他们,他们必须赢得法庭的谴责。在他们的舞台表演中,玛丽的角色由牧师迪奥夫扮演,玛丽母亲的角色由妓女菲利西蒂扮演,还有一个人叫博博是她的邻居。当玛丽和即将强奸并谋杀她的人说话时,她的母亲一直在大声哭喊着她的“糖果和阿司匹林”,并提醒她说该祈祷了。邻居走过来提醒玛丽,如果她继续在黑暗中工作,她的眼睛可能会毁掉。在晚上,玛丽弹钢琴,这是女王认可的一种艺术:“即使在逆境中,在崩溃中,我们的旋律也会唱出来,”她热情洋溢地宣称。玛丽意外地即将临盆。邻居作为接生婆赶到,从她胸前的衣服下拿出了代表五位法庭成员的玩偶。然后她被谋杀了,法庭召开会议谴责凶手。传教士认为受害者应该被封为圣徒,但女王不确定这个想法是否明智。“毕竟,她被玷污了,我希望她能坚持到最后,但她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她的耻辱,”女王思考道。在法庭审判期间,黑人暴动起来,五位法庭成员必须逃脱他们的愤怒。为了缓解他们在道路和田野上行进时的疲惫,传教士批准使用酒精饮料。然而,他们喝醉了。“只有在晚上跳舞,没有人会不打算让我们死。停下。这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每一丛灌木丛都隐藏着一个传教士的坟墓,”传教士警告他们说。法官成功地重新组织了法庭,黑人人口的成员开始颤抖,但他们的领导人之一菲利西蒂站了起来挑战女王。另一位黑人领导人维尔·德·圣纳泽尔透露,他们内部的一个叛徒已被处决,但找到了新的叛乱领导人。法庭成员被包围了,但女王告诫他们要勇敢面对逆境。“向那些野蛮人展示我们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对纪律的重视,以及向那些观看的白人展示我们值得他们流泪,”她宣称。尽管受到这样的鼓励,但法庭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处决了。

荒诞戏剧起源于1940年代的法国,其主要倡导者之一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尤金·艾翁斯科 (1909-1994),他的作品包括 "光头女歌手" (更准确地说是 "光头女主角",1948年) 和 "犀牛" (1959年)。“艾翁斯科和贝克特都致力于向他们的观众传达他们对人类状况荒谬性的感受”(埃斯林,1960年,第671页)。“如果一部好的戏剧(以现实主义风格)必须有一个巧妙构建的故事...[荒诞戏剧]没有故事或情节可言;如果一部好的戏剧是根据人物刻画和动机的微妙性来评判的,那么这些戏剧往往没有可识别的角色,而是向观众呈现几乎是机械的木偶;如果一部好的戏剧必须有一个充分解释的主题,该主题被清晰地揭示并最终解决,那么这些戏剧往往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如果一部好的戏剧要照亮现实,并以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描绘时代的风俗和习性,那么这些戏剧似乎往往是梦境和噩梦的反映;如果一部好的戏剧依赖于机智的妙语和尖锐的对话,那么这些戏剧往往充满了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埃斯林,1974年,第3-4页)。“荒诞的惯例源于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即对生活中意义和目的的感知的消退,这在二战后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很常见。在美国,没有相应的意义和目的的丧失”(埃斯林,1974年,第266页)。与加缪的论文 “西西弗神话” 和萨特的《恶心》不同,这两部作品都从理性角度探讨了非理性,艾翁斯科和其他荒诞戏剧的成员以非理性的方式处理了非理性。“非理性主义戏剧不仅仅是一种攻击理性主义偶像的戏剧,即通过科学实现幸福的无限进步...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旨在成为非理性真实表达的戏剧”(杜布罗夫斯基,1973年,第12页)。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荒诞戏剧或带有荒诞元素的戏剧盛行,以至于在费吉看来(1986年),“只有荒诞剧本身不是荒诞的”(第204页)。
在《秃头歌女》中,“人类状况的图景……是残酷而荒谬的(在没有意义的意义上)。在一个没有目的和终极现实的世界里,中产阶级的礼貌交流变成了脑残木偶的机械化、无意义的滑稽动作。个性和性格,与每个人的灵魂终极有效性的观念有关,已经失去了意义……观众对机械化无意义对话的意义一无所知,就像人物本身一样。这部作品是对礼貌对话语言的解体和化石化的野蛮讽刺(这与反讽完全不同),是对失去所有个性的、甚至性别特征的角色的可互换性的讽刺。这些角色过着毫无意义、荒谬的生活……我认为,……笑声的来源并非来自任何讽刺,而是来自观众自身压抑的挫败感。通过看到舞台上的人机械地表演日常交往的空洞礼仪,通过看到他们被简化为机械木偶在完全的虚空中行动,观众在认出自己在这幅图景中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优于舞台上的角色,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其荒谬性——这会产生狂野的、解放性的笑声——一种基于内心深处焦虑的笑声”(艾斯林,1960 年,第 671-672 页)。这部剧“几乎完全是通过讽刺手法来夸张地描绘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可怕的是……它与每晚在中产阶级家庭里进行的平淡无奇的谈话非常相似……这些角色用礼貌语言的陈词滥调和传统行为的程式化来掩盖他们的无聊和彼此之间的厌恶。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机械化,以至于他们无法学习任何东西”(阿博特,1989 年,第 159 页)。“对话主要以独立的语句的形式出现,很少尝试相互交织……当对话开始时……谈话只不过是意义的破坏……[当] 马丁夫妇被介绍时……对话……源于他们对他们平行存在巧合的相互惊奇。这个过程与未能引起惊讶的不协调相反;在这里,意料之中的事情引起了刻板的惊奇”(格罗斯沃格尔,1962 年,第 53-54 页)。《秃头歌女》呈现了“角色……已经失去了人性……他们甚至没有关于美好时代的记忆,他们在落幕时与开始时一样,似乎不关心任何可能从他们被囚禁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事实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任何囚禁……缺乏任何对他们状况的悲剧感……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很少让人感到惊讶,[比如消防员按门铃],普通的事情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雅各布森和穆勒,1976 年,第 46-54 页)。史密斯夫妇和马丁夫妇之间的谈话源于掌握一门新语言的说明手册(海曼,1976 年,第 17 页)。“剧中日常语言的错位是渐进的,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剧的开头,语言的主要特点是其纯粹的无意义……依翁斯科对语言的攻击的第二阶段涵盖了剧的其余大部分;它从史密斯先生开始说话开始,一直持续到消防队长离开(第十幕)。一旦独白变成对话,就明显看出,这部剧的世界所遵循的逻辑与观众世界所遵循的逻辑毫无关系。在这部分剧中,礼貌对话的形式基本保持不变,但其内容却扭曲而古怪”(莱恩,1994 年,第 31-32 页)。“史密斯夫妇和马丁夫妇……缺乏身份。这些角色彼此模仿,因为缺乏想象力,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当代的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因为他们太渴望取悦别人,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群体之外任何自我意识”(克拉斯纳,2012 年,第 308 页)。“马丁夫妇的问题是,尽管他们被介绍给我们时是夫妻,但他们彼此并不了解……我们看到一对典型的夫妇,结婚多年,却彼此不了解”(韦尔沃斯,1971 年,第 62 页)。“钟声敲了十七下,史密斯太太宣布现在是九点。一个笑话?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它也表明,一天中具体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一小时到另一小时,从一天到另一天,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夫妇的名字叫史密斯:一个非常传统、平淡无奇、中产阶级的名字,适合传统、平淡无奇、中产阶级的人……当史密斯夫妇讨论鲍比·沃森时,资产阶级成员生活中的一致性以及缺乏活力被揭示出来……一个资产阶级与另一个资产阶级之间存在模式没有区别……依翁斯科经常采用一种怪诞的颠倒常态的方式。他通过选取一个熟悉的情景,在那个情景中注入一个使其完全不可能的元素,然后像那个不可能的元素不存在一样写下场景。当马丁夫妇进来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依翁斯科不仅对鸡尾酒会上的谈话进行了精彩的讽刺,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资产阶级沉迷于无关紧要的事物的讽刺。起初,每个人物都试图找到一些深刻的东西来打动别人。结果就是一大堆陈词滥调……史密斯先生走到门口,然后带着消防队长回来……[对门铃事件的解释] 使所有相关人员都满意,因为这是资产阶级解决争议的经典方式:选择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道路……女佣进来,结果是消防队长的爱人。在这里,激情也消失了,因为正如消防队长所说,‘是她熄灭了我最初的火焰’……当消防队长离开时,依翁斯科又呈现了这些人的生活枯燥乏味的另一个例子。聚会上的谈话变成了陈词滥调的连串:‘各人自扫门前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爱人者人恒爱之’——[这些] 彼此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杜科尔,1961 年,第 176-177 页)。莱恩(1996 年)列举了逻辑话语的破坏,包括伪解释(病人死亡是因为手术失败)、错误的类比(一个尽职的医生必须像沉船的船长一样与病人同归于尽)、矛盾(史密斯夫妇已经吃过晚饭,直到女佣进来)、似是而非的推理(当门铃响起时,是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感到惊讶(为什么报纸从来不刊登新生儿的年龄)、人名不可靠(沃森一家)、失语症(一个女人被勒死,因为她以为煤气是梳子)、言语行动矛盾(消防队长说他会脱帽,但不会坐下,而他却做了相反的事情)。这些人物缺乏任何可辨别的动机、理性或内心生活,相反,他们就像木偶……彼此没有区别,也与周围环境没有区别,他们被语言穿透,语言利用他们,而不是相反”(第 32-39 页)。
“犀牛”将幻想与现实融合,通过将角色变成犀牛的荒谬手法,来表达强烈的政治观点,并对社会压迫的本质进行评论。 “犀牛”甚至通过让一个角色问贝兰杰是否读过尤涅斯库的剧本,模糊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而模糊了表现与真实的界限”(萨迪克,2007 年,第 31 页)。“意志的严重瘫痪、想象力的空虚、官僚腐败、恶毒的威权主义、自私自利的利益、自我吹嘘的自我吹嘘,以及最重要的,为了个人利益而无情地取悦他人的需求,对尤涅斯库来说是现代文化困境的象征。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喧嚣,在穿梭于城镇的犀牛群的轰鸣声中得到体现。犀牛象征着缺乏远见的权力过剩;对尤涅斯库来说,我们生活在悲剧的时代……因为我们改变环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死胡同”(克拉斯纳,2012 年,第 313-314 页)。“宿命论和冷漠成为常识……尤涅斯库对犀牛心态的呈现如此令人信服,如此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得到了亲属关系模式的强化……家庭感情凌驾于本应凌驾于家庭感情之上的一切”(霍奇森,1992 年,第 135 页)。“当第一头犀牛打破了社区的礼仪时,他们的评论是令人愉快的不足……他们无法理解这场新入侵的意义,角色们逃离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中,这些事情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的思想太静态了。他们没有原则。他们的想象力很迟钝。他们只能重复生活中正常时期中的陈词滥调。应该指出的是,唯一拒绝变成犀牛的人是头脑最平凡,个性最少的人”(阿特金森和希尔斯菲尔德,1973 年,第 272-273 页)。“贝兰杰……是一个不太可能的英雄:他宿醉、衣衫不整、无方向。他非英雄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可能是,或可以激励任何人的普通人。虽然普通,但他却非凡。通过抵抗犀牛,他是唯一一个保留其独特性的人,并且按照字面意思,没有因为顺从而变得没有人性。此外,他不仅优先考虑自己的个性,也尊重他人的个性,在朋友和同事变身之前,对他们表示安慰和同情。因此,他是唯一一个具有心理深度的角色”(芬伯格,2015 年,第 119-120 页)。贝兰杰“从一个无精打采的懒汉变成了一个热心捍卫一组不可替代的人类价值观的捍卫者”(盖恩斯鲍尔,1996 年,第 102 页)。“他对犀牛的厌恶是发自内心的。‘仅仅看到它们就让我心烦意乱,’他说。他无法表达,他不是用辩论而是用感情反驳约翰对犀牛的辩护”(莱恩,1996 年,第 114 页)。“贝兰杰……软弱、困惑、害怕、酗酒。但他不会屈服”(布鲁姆,2005a 年,第 248 页)。“这部戏剧所传达的是反抗的荒谬性,以及顺从的荒谬性,这是一个无法加入快乐人群的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而这些人没有那么敏感”(埃斯林,1974 年,第 151 页)。“在贝兰杰的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少有值得捍卫的东西。在第一幕的开头,他对他的朋友让承认他感到无聊、疲倦,不适合他尽职尽责地完成的办公室工作……剧中的其他角色在创造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人性方面,并不比贝兰杰更成功……如果意义深长的思考是存在的必要标准,那么逻辑学家在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次要但令人难忘的角色,作为错误三段论的掌握者,比舞台上任何人都没有生命。他自信地无视逻辑限制前提,他得出结论说,四足生物一定是猫……贝兰杰缺乏辨别力的标志是他对逻辑学家的印象非常好……作为犀牛中那些假定角色所遭受的智力萎缩的最后一个例子,考虑一下学校教师博塔德的精神活动。就像几年前那些拒绝承认人类真的登上月球的狂热者一样,博塔德断然拒绝……报纸上关于犀牛存在的报道……当博塔德后来谴责学术界时,他实际上是在进行准确的自我评估:‘大学人士所缺乏的是清晰的思想、观察能力、常识’……在戏剧中,人类文明的剩余部分只是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人类语言碎片,逻辑的相互独立的片段,以人类为名义的空洞人物……因此,当贝兰杰在著名的那段长篇演讲中逐渐完成反抗的姿态时,他的处境很尴尬,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类的辩护……他将如何与犀牛沟通?……无论对错,在他看来它们是有吸引力的,而他对比之下却很丑陋……他最后的几句话与其说是英雄主义或勇敢,不如说是固执的愚蠢……[这出戏的教训可能是:]为了非人性而存在的个人主义不是美德……兽性作为非理性人类存在的替代品不是缺点”(丹纳,1979 年,第 210-214 页)。“让在谴责贝兰杰的道德松懈,而教授则在舞台的另一边进行逻辑论证,他们最终说了完全相同的话,以完美的和谐相互呼应,尽管他们的意图完全不同……然而,犀牛不连贯的咆哮能够直接与那些开始感到被诱惑加入它们的人交流”(布拉德比,1991 年,第 76 页)。贝兰杰是唯一一个发生改变的角色。“只有他一个人不愿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从冷漠到参与,从濒死到生,他的转变是随着他对一个又一个角色关于犀牛病的奉承的辩论而描绘出来的”(雅各布森和穆勒,1976 年,第 66 页)。相比之下,杜达德认为犀牛病是“社区精神战胜无政府主义冲动”的标志(海曼,1976 年,第 110 页)。约翰“一心想要保持表面现象……最虚伪和自以为是……挑剔,吹嘘自己想象中的优于贝兰杰……第一个放弃自己人性……博塔德是最傲慢、固执、不讲道理……他最初断然拒绝犀牛的故事……但……有强烈的责任感……遵守任何或任何拥有权力的人……杜达德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平静地做出反应……敦促最好的做法就是简单地忽视这些野兽,让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黛西……选择“自然”的生活,称犀牛为“真正的人类”(雅各布森和穆勒,1976 年,第 42-46 页)。“博塔德和年轻的暴发户杜达德一样心胸狭隘,固执己见。博塔德怀疑且固执,他确信犀牛病的瘟疫是一个右翼阴谋,由媒体支持,被大众所吞噬。博塔德否认镇上有犀牛的存在,称之为‘你们的宣传’和‘臭名昭著的阴谋’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为了赚钱而采取的策略。博塔德指责记者捏造事实:‘他们不在乎他们为了出售他们可怜的报纸和取悦他们所服务的老板而编造什么’”(昆尼,2007 年,第 46 页)。“这出戏,尽管主人公蔑视兽性,但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苦涩的、几乎绝望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是荒谬的,尤涅斯库告诉我们;它们与生活的真相(即混乱)几乎没有关系”(克鲁曼,1966 年,第 86 页)。相比之下,贝内特(2011 年)提出,“极权主义政权取得成功的很大程度上是大众的 complacency。但犀牛没有已知的捕食者(除了人类),而且可能是有史以来人们最不愿意想到可以被赶来赶去的动物之一……不同的物种可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特征,从独居到群居……一个人如何在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群体中保持个性?……贝兰杰承担了西西弗斯式的使命……我们可以通过反抗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并创造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生存目标”(第 95-98 页)。“早期的英雄们认为他们在为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而奋斗,希望支撑着他们在追求中。在尤涅斯库的宇宙中,贝兰杰拒绝投降没有赋予任何宇宙或宗教意义”(阿博特,1989 年,第 165-166 页)。“因此,犀牛成为对社会中的人类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刻画,任何社会,都被他的同类排斥,原因是他无法完全理解”(帕塞尔,1986c 年,第 1002 页)。“在戏剧中,就像在小说中一样,……衰弱的标志是目前不愿意(我认为,源于无能为力)创造角色。某种反人道主义与这种品质有关,即使在像犀牛那样明确表达了对人类异化的担忧的作品中,人们也能感受到这种品质的存在”(加斯纳,1968 年,第 502 页)。
“尤涅斯库是一个了不起的模仿者,一个愤世嫉俗的怀疑论者,一个几乎不可抑制的快乐虚无主义者;他在喜剧和悲剧中都一样有效。他能够挑战反思,同时激怒感官或用他的滑稽表演来挠我们的痒处,并能够在几乎同一口气中让我们沮丧和娱乐”(加斯纳,1960 年,第 261 页)。“当他的角色体验到轻盈、快乐、短暂时,它总是孤独的情感。他们无法从与他人的共同欢乐中获得快乐。事实上,几乎总是社会存在的压力和侵入性破坏了他们内心的幸福感”(布拉德比,1991 年,第 81 页)。
"秃头歌剧"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50 年代。地点:英国伦敦。
文本位于 https://macaulay.cuny.edu/eportfolios/smaldone2011/course-readings/
史密斯太太喋喋不休地谈论家事,史密斯先生则啧啧称奇。他从报纸上读到鲍比·沃森去世的消息。史密斯太太特别提到,她现在想到的是鲍比·沃森的妻子,鲍比·沃森。史密斯夫妇建议,鲍比和鲍比·沃森的孩子,分别由鲍比和鲍比·沃森的叔叔和婶婶照顾,这样寡妇就可以再婚。“她有中意的人吗?”史密斯太太问道。“是的,鲍比·沃森的堂兄。”史密斯先生肯定地说。“谁?鲍比·沃森?”他的妻子问道。“你指的是哪一个鲍比·沃森?”他反问道。“老鲍比·沃森的儿子,也是已故鲍比·沃森的另一个叔叔。”她回答。“不,不是那个。”他说。“鲍比·沃森,老鲍比·沃森的儿子,鲍比·沃森的姑姑的儿子。”在确定了这件事后,他们邀请的客人来了,一对彼此不认识的男女。在交谈中,两位客人惊讶地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直到意识到他们是夫妻。门铃响了。史密斯太太起身去看看是谁,但没有人。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直到愤怒的史密斯先生起身看到一个消防员站在门口,他已经在那里等了45分钟。当被问及如何解释时,消防员透露,前两次铃声响起时他什么也没看到,但第三次是他自己按响铃声,然后躲起来,当作一个玩笑。他背诵了一些实验性的寓言,例如狗和公牛:‘另一头公牛问另一条狗:你为什么不吞下你的鼻子?—对不起,狗回答,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一头大象。’ 他们的谈话被史密斯夫妇的女佣玛丽打断,她想表达自己的轶事,但这两对夫妇对一个区区女仆这样做感到反感。消防员认出玛丽是他失散多年的恋人,一个“熄灭了我初次火焰”的女人,他说,玛丽也同意是“他那小小的喷泉”。当她试图背诵一首名为“火”的诗时,史密斯夫妇将她赶出了房间。在离开之前,消防员问起了那个秃头的歌剧女主角。“她像往常一样把自己遮盖起来。”史密斯太太回答。消防员离开后,这对夫妇越来越难以理解对方,然后迷茫地四处奔走。
"犀牛"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50年代。地点:法国巴黎。
文本链接: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167320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58383
约翰责怪他的朋友贝兰热过度饮酒和生活无序。突然,他们之间的谈话被一只在街上奔跑的犀牛打断了。他们讨论了这只动物可能来自哪里,但每个建议都比另一个更不可信。贝兰热的同事黛西过来谈论同样的话题。又一次,谈话被一只犀牛打断了,这次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奔跑。一位家庭主妇过来抱怨犀牛压死了她的猫。约翰、贝兰热和黛西讨论了它是否是同一只犀牛还是不同的犀牛。一名杂货商认为是同一只,但约翰不同意,解释说前一只有两根角,因此是亚洲犀牛,而第二只只有一根角,因此是非洲犀牛。考虑到它们奔跑的速度,贝兰热质疑他的朋友是否能可靠地数出角的数量。“此外,它身上沾满了灰尘。”他补充道。在他看来,约翰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学究。约翰感到被冒犯了。一位老人插话询问,那只独角犀牛真的是非洲的吗?约翰和贝兰热就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争吵。根据黛西的说法,两个人都错了。“亚洲犀牛只有一根角,非洲犀牛有两根角,反之亦然。”杂货商断言。约翰愤怒地离开后,贝兰热对自己的态度以及他朋友的态度产生了疑虑。“最小的异议都会让他怒火中烧。”贝兰热宣称。一位逻辑学家过来表示,即使第一只犀牛有两根角,第二只只有一根角,也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两只犀牛是不同的,因为第一只犀牛可能失去了一根角。在贝兰热工作的办公室里,关于犀牛是否存在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同事波塔德认为它们是虚构的,这种观点冒犯了贝兰热和黛西。相反,另一位办公室职员杜达德,爱着黛西,相信她的目击证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了多少。”波塔德谈到贝兰热时说道。在街上看到一只犀牛后,另一位办公室职员,比夫斯泰克夫人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一只犀牛破坏了办公楼的楼梯,导致员工无法出去。然而,波塔德继续否认它们的存在,直到他亲眼看到一只犀牛。比夫斯泰克夫人认出门口的一只犀牛是她的丈夫。贝兰热看到了一只长着两根角的动物,但仍然不确定它是亚洲的还是非洲的(不知道如果它是白色或黑色,那么它就是非洲的)。与此同时,部门主管巴特弗莱鼓励所有员工返回工作岗位,而黛西则打电话求助。比夫斯泰克夫人抓住机会,从高层直接跳到犀牛背上,与她的犀牛丈夫一起逃跑。波塔德假装知道犀牛出现背后的原因,但不愿意在此时透露。在紧急情况下,消防员赶到,将员工从大楼中带出来。贝兰热对自己和朋友的争吵感到不安,于是去约翰家道歉,但当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在他眼前变成犀牛时,他感到很害怕。巴特弗莱和杜达德也随着人群的增长而遵循同样的模式,黛西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广播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后。贝兰热不惜一切代价抵制这种转变,他抵抗了变成其中之一的诱惑。
塞缪尔·贝克特
[edit | edit source]
塞缪尔·贝克特 (1906-1989) 继续或完善了荒诞剧,有人会说,用 "等待戈多" (1952)、"终局" (1957) 和 "快乐的日子" (1961)。
"Waiting for Godot" “marked a clear break with the dramaturgy of the 1940s and...established a new frame of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theatre...Where ‘Waiting for Godot’ seemed initially incomprehensible to its first...audiences...its meanings are now self-evident” (Innes, 2002 p 307). “Who...is the unseen Godot? To some, he is death, to others, life, to a few, nothing...one could probably settle on Godot as standing for God...His absence does not signify negation...but...infinite possibility” (Bennett, 2011 pp 27-43). “Vladimir and Estragon...are clearly derived from the pairs of cross-talk comedians of the music hall...Vladimir remembers past events, Estragon tends to forget them as soon they have happened. Estragon likes to tell funny stories, Vladimir is upset by them. It is mainly Vladimir who voices the hope that Godot will come and that his coming will change their situation, while Estragon remains skeptical throughout” (Esslin, 1974 pp 26-27). “Vladimir thinks more, he is more cultured, his anguish is more intellectualized, he is more hesitant and demanding in his choice of words. Estragon is more spontaneous and more lethargic, he is more childish, he sulks more, he is more eager for protection, he is more egoistical and more obstinate, he holds to his own vocabulary and refuses Vladimir’s nuances. Vladimir is more restless, more active, Estragon more inert. Vladimir has the responsibility: he is in charge of the carrots, radishes, and turnips that constitute their meals. Estragon is more the victim: he is kicked by Lucky. While Vladimir tries to make conversation with Pozzo and to seem well-bred, Estragon listens only because he is threatened or ordered to; otherwise, he independently follows the flow of his own thoughts” (Guicharnaud, 1967 p 236). "Didi is the contemplative, the listener, the seeker, the one expecting messages, the ascetic, the one who suppresses his physical side, while Gogo is the active, the non-reflective, the one who tries to wipe the tears from the eyes of sufferers, who must eat when he is hungry, and who bellows when he is hurt. Neither can do without the other" (Baxter, 1965 pp 10-11). “Estragon, who's nickname is Gogo, is of the earth. His name is French for ‘tarragon’, an aromatic herb used as a seasoning in pickling. His obsession with his ill-fitting boots that cause him pain indicates that he is close to or of the earth. Gogo also goes and comes. He is the wanderer who always stumbles back to his companion Didi. He can be sarcastic and skeptical, but mostly he is resigned to an inevitably unhappy fate. Vladimir, whose nickname is Didi, continually looks and feels into his hat, seeking cooties or some other irritant, just as Gogo is tormented by his ill-fitting boot. He is more rational and less emotional than Gogo. Vladimir seems more in touch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more aware of his immediate world. He is better spoken than Gogo, and he sings in both acts.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pair, and, significantly, he is the one who most believes in Godot...Pozzo is a sadist, enjoying his power over his slave, Lucky, but he is also weary of the relationship. After all, a master is always tied to the slave who serves him…Pozzo stands for capitalism exploiting the worker, Lucky. The derby or bowler hat enforces this consideration. Pozzo is all materialism, concerned about his baggage, his comfort, his food, his pipe, and his watch. Lucky has nothing but his hat and his burdens. Lucky is a slavish masochist who does not want relief from his pain and thus attacks Estragon. The fact that he does not take advantage of Pozzo's blindness in act 2 to escape or kill his enslaver indicates that he has need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even the punishment. Lucky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the exploited worker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but also the tormented intellectual made ineffectual by that society. It may be that Pozzo and Lucky are yin and yang in their relationship: part of one personality or entity” (Sternlicht, 2005 pp 54-55). “Serious subject matter is presented in music hall form...Much of the surface is taken up with farcical satire of conventional social behavior. Pozzo, for example, is unable to take a simple action like sitting down without an attendant barrage of ceremony, and the two tramps are always trying to strike up what will pass for a polite conversation, using catch-phrases like Vladimir’s: ‘this is not boring you, I hope?’” (Gascoigne, 1970 p 186). "What makes the play more than just a pastiche of clown and music hall comedian is partly the philosophical overtones and partly the self-conscious elements...The characters watch themselves act, reflect at the very moment of acting on the significance, or absence of significance, of those actions” (Bradby, 1991 p 59). “Beckett’s extraordinary feat of blending pathos and comedy is accomplished b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 characters who are, despite their bloviated portentousness and inane banter, filled with enormous charm. They are hilarious as they are tragic, exquisite amalgams of clownishness and grandeur. They can be pompous and stubborn, yet just as quickly brought down to earth with humility and despair” (Krasner, 2012 pp 343). According to Durán (2009), The play "reflects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For Camus, the absurd issues from the clash of two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rational man and an irrational world...It soon becomes clear that Vladimir and Estragon live in a world wholly devoid of reason. The characters engage in pointless acts, the dialogue abounds in non-sequitur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memories are short. Characters often forget whom they know or what they know. In Beckett's play, things happen not according to any logic or order, but as a result of sheer fortuity...Vladimir and Estragon thus find themselves disoriented and alienated from the irrational world they inhabit...Consequently, the two characters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and energy devising ways to fill the emptiness of their mundane lives...Camus explains that one continues to live this type of absurd existence largely out of habit...But Camus warns that the protective walls of habit can unexpectedly fall away making one suddenly aware of life's absurdity...Thinking poses a danger because it can expose one to that 'suffering of being' provoked by a consciousness of the absurd...Suicide affords one means of escape...After learning from the young messenger that Godot will not come that day, Estragon gazes at the tree and laments... He asks Vladimir to remind him to bring a rope the next day and recalls a past attempt at suicide...The rejection of suicide still leave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the other opposing term: an irrational world. Despite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one may choose to view the world as truly rational. Camus calls this strategy 'the philosophical suicide'...By adopting systems of belief such as religion, philosophy, astrology, or what have you, one imposes a false logic and order on this world...Lacking the courage to commit physical suicide, Vladimir and Estragon find solace in philosophical suicide. They see their hope in the coming of a Godot, someone who will satisfy all their wants and needs...No matter what occurs, Vladimir and Estragon cling tenaciously to their hope in Godot's appearance...As a result, the two tramps end up doing nothing...Camus believes that an authentic response to the absurd resides in neither physical nor philosophical suicide...Rather than elude the absurd, one must not only accept but also sustain its truth, constantly confronting its reality through what Camus calls a metaphysical revolt...In the final pages of his essay, Camus illustrates his concept of 'revolted man' through the character of Sisyphus...[who] chooses instead to embrace his fate, fully conscious of all that that implies. [But the tramps] incarnate, in fact, the exact opposite of Sisyphus. Rather than embrace their reality, the two tramps use every means available to evade it" (pp 982-989). “Vladimir and Estragon play the game of waiting for an entity that they have invented to save them from the unknowable. They have even hired a boy/priest to reassure them at regular intervals that they are not waiting in vain. Meanwhile they eat, sleep (and have nightmares), engage in futil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and otherwise parody human existence” (Wellwarth, 1986 p 71). "In Waiting for Godot, auditory and visual scenic means convey the tension between comedy and tragedy to the audience. Act Two ends in nearly an identical way to Act One. Estragon and Vladimir discuss suicide and separation. A tree, the only permanent prop in the play, has sprouted four or five leaves. However, what might signify the meaningful fullness of life the participation of humanity in a scheme of things larger than itself, a metaphysical reality 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 form of tragedy is reduced to mere occurrence" (Como, 1989, pp 68-69). Brater (2003) emphasized the movement of the play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universal, as in Vladimir's following comments to his fellow tramp: 'let us do something while we have the chance. It is not every day that we are needed. Not indeed that we are personally needed. Others would meet the case equally well, if not better. To all mankind they were addressed, those cries for help still ringing in our ears! But at this place, at this moment of time, all mankind is u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Let us make the most of it, before it is too late'" (p 145). “The clearest statement of Beckett’s belief in the uselessness of thought is in the tremendously effective scene of Lucky’s tirade in Waiting for Godot. Beckett here implies that it is only in modern times that man has become impotent in thought and action” (Wellwarth, 1971 p 46). Lucky’s tirade "is one magnificent moment when a bestially slave-driven underdog bursts into an incoherent speech which gives an extraordinary Joycean impression of overcharged meaning" (Williamson, 1956 pp 69-70). “We have no superficial allegories and personifications of abstractions, but characters who are both symbolic and real in a situation which is a metaphor of the human condition...This is the true metaphysical Pascalian and Kierkegardian absurdity and nonsense of life without God or purpose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remote from the dehumanized, incoherent world of Ionesco...The Pozzo-Lucky relationship is the mirror of human degradation and shallowness. Pozzo hides his insignificance and hollowness under a cloak of ritual gestures and ceremonies which are part of the social apparatus of power...Lucky is merely an object, a thing, and his life is reduced to mechanical reactions; he not only serves Pozzo, he has also to think for him; he is therefore materially and spiritually Pozzo’s slave and has no individual existence” (Chiari, 1965 pp 68-74). The tramps “appear as a social unit outside society...like prisoners free to amuse one another...It is as though they ad lib for their very lives...The play takes up themes of many kinds-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ical- without any of them to become the drama’s motif, and with a fierce comic opposition to their pretensions...Pozzo and Lucky are emissaries from the realm of time and from the life of society, with its institutionalized relationships, its comforts and delusions, above all its thirst for hierarchies...the principles of huma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delusory, ultimately disastrous, but maintained by them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lives...Whenever a character appears to be feeling some definite emotion or to have entered some decisive area of commitment, it is all undone by an opposite remark, a corrosive scornfulness, a physical jape” (Gilman, 1999 pp 242-250). “The word ‘divine’, used three times in the play, is spoken not by the seekers for Godot but by the slave commanded to ‘think’, the broken-down scholar, Lucky, in his wild meditation on the existence of ‘a personal God [including] referring to the ‘divine Miranda’, which points us to Shakespeare’s heroine in The Tempest, someone able to suffer ‘with those who for reasons unknown but time will tell are plunged in torment’. That she could so feel for total strangers understandably makes her ‘divine’ for the maltreated Lucky” (Worth, 2006 p 239). “Sober expression of misery is rare in this nearly wholly stichomythic play whose words are never allowed to inflate the period. The words remain simple, idiomatic, slangy” (Grossvogel, 1958 p 329).
“终局” “揭示了一种单一的基调和一种执着的目的,它令人敬畏和困惑……在“终局”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而那什么正是重要的……苦涩很重要……被困的感觉很重要……哈姆的蔑视的强度很重要……哀歌般的氛围很重要”(加斯纳,1960 年第 256-258 页)。“哈姆瘫痪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的仆人克洛夫无法坐下……一些巨大的灾难,剧中人物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杀死了所有生物……哈姆不修边幅。克洛夫是秩序的狂热者。哈姆的父母是怪异的感情上的白痴”(埃斯林,1974 年第 41 页)。哈姆可能是锤子的缩写,克洛夫可能反映了“clou”或钉子,从中可能得出奈尔(或钉子)和纳格,来自德语翻译“Nagel”(门德尔森,1977 年)。“纳格和奈尔在他们的垃圾桶里似乎是棋子;克洛夫,带着他任意限制的动作(‘我不能坐’)和他的骑马背景(‘你的巡逻呢?一直步行?’ ‘有时骑马’)类似于骑士,他完美的立方体厨房(‘十英尺乘十英尺乘十英尺,很好的尺寸,很好的比例’)类似于棋盘上的一个方块,被翻译成三维。他来回移动,进入和走出它,来到哈姆的身边,然后退却。在终局结束时,棋子永远保持静止,克洛夫准备最后一次离开棋盘,现状永远受到透过窗户看到的预期棋子的威胁,国王哈姆被遗弃在将军状态”(肯纳,1961 年第 156-157 页)。“不断地提到游戏、玩耍和戏剧的问题。哈姆在他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独白中用‘我— [他打哈欠]—要玩’ 开头。对于克洛夫的‘有什么能留我在此?’ 的问题,他回答‘对话’。哈姆在了解潜在的戏剧惯例和表演规则的情况下表演,‘既然我们就是这样玩它的……我们就那样玩它’。他教克洛夫:‘旁白,猴子!你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旁白吗?[停顿] 我正在为我的最后一个独白热身’。他以戏剧性的方式开始和结束这部戏:在开头,他让幕布升起(‘他从脸上拿开手帕’)而在结尾,他让它落下(‘他用手帕遮住脸’”(菲舍尔-利希特,2002 年,第 331 页)。这种类型的自我意识是后现代风格的缩影,与以前时期缺乏自我意识形成对比。“哈姆关心一天中所有行动都要精确地进行,尤其是他对被置于房间的正中心的痴迷,呈现出一个试图建立自己尊严和重要性的人的形状,这种尝试在他的环境中变得荒谬”(布拉德比,1991 年第 70 页)。“熵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力量耗尽与意志的坚定之间的张力,身体限制或无力与玩耍的能量之间的张力——僵局的戏剧张力——在“终局”中至关重要。这种张力在哈姆和克洛夫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最后快要死了……哈姆请求‘几句话’……克洛夫的回答是关于艺术和秩序之美的愿景……哈姆无法与之匹敌,他认输了……克洛夫说他要离开牢房,离开结构,但我们看到他站在阴影中……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哈姆,直到最后……哈姆……以为自己独自一人在结构中,独自一人死去”(罗森,1983 年第 275-276 页)。
“幸福的日子”是贝克特另一部关于人类悲惨命运的挽歌,人类被归结为荒谬的僵局,从这个僵局,人类只能走向更糟糕的境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人类韧性和坚定意志的赞颂,他们决心维护信仰或妄想的内心防线,抵御失败,不屈服于感伤,作家用持续的讽刺来抵御这种感伤,因此,人类的英雄主义也显得像是一种荒谬的自欺欺人能力”(加斯纳,1968 年,第 504 页)。“一方面,温妮在她可怕而绝望的困境中如此乐观,这很悲剧,另一方面,这也很有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乐观是纯粹的愚蠢,作者似乎对人类生活做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评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温妮在面对死亡和虚无时的乐观,是人类勇气和高尚的体现,因此,这部戏剧提供了一种净化,温妮的生活确实充满了幸福的日子,因为她拒绝被沮丧”(埃斯林,1974 年,第 59-60 页)。“温妮……被埋到腰部,后来被埋到脖子,保持着逻辑学家、语法学家的超然态度,超然于她的困境……尽管地球现在转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在炎热的白天,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自燃的威胁(“哦,我并不一定是指突然着火”),但她还是有些不安地考虑着,她刷梳的头发或头发是否应该被正确地称为“它们”或“它”(“刷梳它?听起来有点不妥”),她觉得弄清楚“猪”的正确定义比一天的痛苦更有意义”(肯纳,1961 年,第 93-94 页)。“温妮最奇怪的特征是她快乐……温妮已经认命了,渴望吞噬任何旧的谎言,甚至是诗歌,利用任何“旧词枕头”来枕她的头……温妮是一个受害者,人类状况的受害者……她拥有生存的常用慰藉:她给自己讲故事,她有她的包,她有各种各样的物品……然而,她对抗荒谬的最强大武器是她漠不关心”(科伊,1986 年 a,第 163-164 页)。在温妮的歌声中,欢乐寡妇圆舞曲平淡无奇的歌词,被它轻快的曲调和歌曲与残暴地被禁锢的歌手之间的反差所提升,进入另一个维度,在那里,舞蹈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就像婚礼当天的回忆和曾经说过的话语一样”(沃思,2006 年,第 242 页)。
“尽管贝克特的失败戏剧充满了智力游戏和文本间的相互参照,但它依然是严谨的非概念性的。它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思考,而是让我们感受,创造出能够深入皮肤,产生强烈、错位体验的引人入胜的氛围”(拉弗里,2015 年,第 28 页)。
"等待戈多"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50年代。地点:法国。
两个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这个人答应过会来,但还没有到。在等待的过程中,这两个朋友试图娱乐自己。然而,时间过去了,戈多还是没有出现。为什么?他们是否记错了约定日期?他们是否来对了地方?埃斯特拉贡饿了,但弗拉基米尔拿出一根胡萝卜,大部分都吃掉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根胡萝卜,”他在几乎持续不断的无聊状态中说道。他们的等待被波佐和拉奇的到来打断,拉奇似乎是波佐的仆人,如果不是奴隶的话,就被一根绳子牵着,走在波佐的后面。这种关系似乎让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感到震惊,但他们并没有干预。更糟糕的是,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开始对那个显然是哑巴的拉奇施加与他对主人所受的同样可憎的待遇。但拉奇并不是哑巴。他最终爆发出一段没有标点符号的独白,其中很多部分是语无伦次的,没有任何结果,之后他和波佐一起离开了。一个年轻的男孩突然出现,是戈多派来告诉他们,他明天会来。弗拉基米尔似乎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男孩否认了。第二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样,除了树上长出了几片叶子。类似的滑稽剧式的对话被重复了,却毫无用处。尽管弗拉基米尔提到他们前一天在同一个地方等待,但埃斯特拉贡不记得了。波佐和拉奇走了进来,很快便摔倒了,但两个流浪汉都没有帮助他们,尽管弗拉基米尔说有必要这样做,埃斯特拉贡也愿意在得到钱的情况下帮忙。波佐现在失明了,拉奇哑巴了,虽然波佐不记得什么时候发生的这种不幸。他们继续上路。男孩回来了,留下了和前一天一样的消息,却不记得自己前一天说过什么。作为唯一一个似乎记得的人,弗拉基米尔的生存似乎更加徒劳。两个朋友决定在树上吊死自己。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勃起。埃斯特拉贡解开腰带,像滑稽剧一样,裤子掉了下来。他们还没来得及尝试,腰带就断了。他们放弃了。他们决定离开,但没有动。
"终局"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50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地址:https://pdfcoffee.com/endgame-by-s-beckett-pdf-free.html https://edisciplinas.usp.br/pluginfile.php/3346220/mod_resource/content/1/ENDGAME%20BY%20SAMUEL%20BECKETT.pdf
汉姆从脸上取下一条血迹斑斑的手帕。他双目失明,无法站立,由克洛夫服侍,克洛夫有视力,但无法坐下。在打哈欠的时候,汉姆问道:“我的痛苦比这更高尚吗?”汉姆害怕克洛夫可能没有让他承受足够的痛苦,但听到保证说他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后,他感到宽慰。汉姆的父亲纳格住在垃圾堆里,要他的婴儿粥。“该死的祖先!”汉姆愤怒地喊叫着。他命令克洛夫给他一块饼干。汉姆绝望地认为大自然已经遗忘了他们,但克洛夫纠正他说,不再有大自然了。纳格抬起垃圾堆的盖子,试图亲吻他隔壁垃圾桶里的妻子内尔,但没有成功。当纳格嘲笑汉姆的痛苦时,内尔责备他。“没有什么比不幸更有趣了,我承认,但……”她说道,却无法说完。突然,汉姆决定要被放在房间的正中央。克洛夫费了很大劲才终于满足了他的愿望。汉姆接下来要求他用望远镜向外看,但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片灰色的景象。汉姆又有了另一个可怕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吗?”他大声自问道。当一只跳蚤困扰着克洛夫时,汉姆命令他立即杀死它。“人类可能会从那里重新开始,”他警告道。他接下来要求一个导尿管来排出尿液,但克洛夫还没来得及拿来,他就尿在了自己身上。然后他要求克洛夫摆好一只恳求的黑玩具狗的正确位置。不久之后,内尔去世了,纳格哭了起来。汉姆多次问克洛夫是否该吃止痛药,最后发现没有止痛药。继续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克洛夫离开了。汉姆吹了吹口哨,但没有人回应,他就扔掉了口哨,用一条血迹斑斑的手帕捂住脸。
"幸福的日子"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60 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地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happy_days_a_play_by_samuel_beckett
温妮直立地半埋在一个土堆里。一个来自未知来源的铃声是她开始新一天的信号,她从包里拿出梳子、牙刷、牙膏、手帕、口红、指甲锉、开胃药、眼镜和左轮手枪。拿出这些东西后,她亲吻了左轮手枪。她的丈夫威利住在土堆后面的洞穴里,阅读报纸和明信片,并在阴茎上涂抹舒缓溶液。她能听到他,但看不到他。她在阳伞下,以防阳光照射过度,继续进行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例如在同一时间唱歌。当她喋喋不休时,威利似乎没有在听,所以她有时不得不打他来引起他的注意。来自未知来源的音乐声响起,她欣喜若狂。威利没有做出太多贡献,但至少他设法为她定义了“猪”这个词。天气很热。最终,阳伞因过度高温而着火,但她仍然乐观地认为,这一天可能会顺利结束。在一天结束时,铃声再次响起,这时她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放了回去,除了枪。温妮对物质要求很少,感到很满足。“这将是另一个幸福的日子,”她总结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同一个唤醒铃声响起,她现在被埋到脖子,无法再操作任何物品,但她仍然确信,这将是她的另一个幸福的日子。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威利的声音了,但她相信他仍然能听到她,或者,即使听不到,他无论如何仍然在那里。“哦,毫无疑问,你已经死了,和其他的人一样,毫无疑问,你已经死了,或者你离开了,抛下了我,和其他的人一样,这并不重要,你就在那里,”她说。出乎意料的是,威利终于出现了,朝她走来,或者朝枪走来,但在到达枪之前,他从土堆上摔了下来。他设法喊出了她的名字,她欣喜若狂。“温妮!哦,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这将是另一个幸福的日子!毕竟。到目前为止,”她为自己总结道。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
[edit | edit source]
荒诞戏剧的另一位倡导者是西班牙出生的费尔南多·阿劳巴尔 (1932-?),他以“汽车坟场”(1959 年),“格尔尼卡”(1959 年) 和“盛大仪式”(1963 年) 而闻名。与英国厨房水槽派一样,荒诞派作家最好的作品似乎都出现在他们戏剧生涯的早期。他也是“恐慌剧”的倡导者,用阿劳巴尔自己的话说,将“机会、记忆和意外”融入其中,以破坏官方写作(Drumm, 2009 p 437),“以潘为名,并以酒神支配为原则”(Farmer, 1971 p 155)。“荷马赞歌第 19 首,题为‘致潘’,提供了对这位神的最完整描述,阿劳巴尔从这位神那里得出了“恐慌”一词。潘是牧羊人的神,住在高山上……[不像阿波罗的甜美音乐,潘演奏的是]“原始物质……用他粗陋的芦笛演奏着野蛮的曲调”(Arata, 1982 pp 7-8)。
在“汽车坟场”中,“坟场成为文明崩溃的象征,是科技社会道德毁灭的象征”(Podol, 1978 p 46)。“这个微观世界中这些人物用来应对日常生活无意义的中心视觉形象是坟场本身,那里充满了报废的汽车,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破坏性”(Podol, 1988 p 134)。“原始的善良以及它引发的激情是《汽车坟场》的主题,在作品中,阿劳巴尔用极大的想象力,把舞台上挤满了悲惨而积极的性行为的社区,他们居住在坟场里一堆堆报废的汽车中。在他们可怜而滑稽的中间,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小号手,还有两位其他音乐家。这个英雄当然是一个屠夫,每当他感到冲动时,但他被称为埃玛努,最终被背叛和殴打,最后被绑在自行车上抬过舞台,一个女人用一块布擦他的脸。耶稣激情的移置过于明显,象征的幼稚削弱了剧本的力量,否则剧本会充满创造力和意义”(Guicharnaud, 1967 p 186)。“也许他更像是一个有远见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剧作家,[阿劳巴尔]有忠于他所看到的优点:他那匿名语言 - 正确但没有风格,与亚当诺夫非常相似 - 使他无法作弊。他看到了汽车坟场,它的角色、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形状;但当他用埃玛努-基督象征击打我们时,效果就被破坏了”(Guicharnaud, 1962 p 119)。“循环模式从剧本开场的对话中就建立起来了。阿劳巴尔把当代生活的缩影,汽车废车场,挤满了废弃的汽车,每一辆都住着看不见的顾客。当客人在第一幕中安顿下来准备过夜时,他们像往常一样被女仆迪拉拥抱,我们很快就知道警察“又回来了”,他们正在寻找三个音乐家,这些音乐家像往常一样会逃跑……在对话中发现的循环结构被延续到剧本的非语言方面。不断地穿过舞台,赛道跑步者和警察与强盗的运动是空间辩证法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次未完成的朝圣,因为这个圆圈没有中心,没有解决方案,没有最终目的地。跑步者拉斯卡和提奥西多正在进行一次空虚的游历,它没有通往任何地方……两种对立的力量相互追逐:一方面是纯洁和无辜,另一方面是腐败和妥协。后者,就像拉斯卡和提奥西多,毫无疑问地屈服于规章制度,屈服于三份一式填写的表格,屈服于严格的训练和纪律。他们致力于维护现状。即使是住在废车场里的弃儿也属于这个世界,模仿着它的仪式,这些仪式在米洛斯热心的照料下变成了怪诞的模仿。他们与强者团结起来,反对埃玛努的纯洁。似乎在顺从的保护下,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终于达成了休战……迪拉在这个世界中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只有她清醒;只有她既了解埃玛努的纯洁,也了解她生活的堕落。她也“想做好事”,渴望纯洁,但她知道已经太晚了……她保护埃玛努,把他藏起来,拒绝为了奖赏而背叛他。然而,她对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盲目感到厌烦”(Luce, 1974 pp 33-35)。“那些流浪者……都是成年的孩子,无辜的凶手、窥视者和展览狂。他们喜欢撒尿和做爱。他们讨厌警察,却不断被警察追捕……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迪拉时,她像一位伟大的母亲一样四处走动,强迫所有住在这里的人晚上睡觉。然后,她把自己交给了任何想要她的男人……迪拉冷嘲热讽地提醒埃玛努,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做好事只会惹麻烦……她是对的……当他在人群中给一些人喂了几条沙丁鱼和一些面包时,其他人变得嫉妒了。最终,他的颠覆活动导致了警察的追捕,以及他被朋友之一的背叛……通过埃玛努,阿劳巴尔……揭穿了慈善和爱的基本基督教伦理……他的善举对他所在的社区几乎没有影响,我们假设,对他们没有任何持久的影响”(Donahue, 1980 pp 12-15)。埃玛努代表着以马内利的缩写形式,即耶稣基督。他的先例是相似的,出生在马槽里,木匠和玛丽的儿子,用鱼和面包喂食人群,被一种食物记住,被一个吻背叛,并以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位置暴露出来。“剧中的人物变成了现代的圣经人物……遵循中世纪神秘剧和奇迹剧的传统……拉斯卡和提奥西多……变成了会逮捕耶稣的罗马士兵(警察),提奥西多也扮演了彼拉多的角色,模仿他洗手的那一刻,福德雷……扮演了彼得的角色,说出三次否认耶稣的话,迪拉……首先像玛利亚·马达拉,后来变成了维罗妮卡,为耶稣洗脸,托佩……扮演了犹大·伊斯加里奥的角色,米洛斯……最后变成了西蒙,为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Arata, 1982 pp 33-34 and p 68)。“米洛斯通常控制着迪拉;他在几个场合惩罚了她,一次是因为她没有提供性恩惠,另一次则是非理性地惩罚她,因为她恰恰做了那样的事。然而,迪拉在剧本中的另一个时刻,咄咄逼人地威胁着胆小的米洛斯,要惩罚他。戏剧的循环结构源于拉斯卡和提奥西多的身体运动。这两个角色以寻求新的世界纪录开始和结束作品,但角色颠倒了。他们的关系反映了雄心勃勃的母亲的坚强意志,以及男性在将自己与女性比较时,为了应对自卑感,而需要在身体上表现自己的需要。拉斯卡和提奥西多也代表着国家的压迫性。在剧本的结尾,他们局限而窒息的路线的荒谬性得到了肯定,他们变成服务于体制的警察的可能性保持不变……埃玛努犯了谋杀罪和其他社会不能接受的罪行。然而,他确信自己会被赦免,因为他记住了善良的意义……如果基督可以被认为是爱,那么他和那种情感都被汽车坟场那个机械化、非人性化的世界所废除了。坟场本身构成了一种中心、视觉上的文明崩溃象征”(Podol, 1986a pp 125-126)。
在“格尔尼卡”中,“法恩丘和莉拉既是西班牙内战和所有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又是导致毁灭性争吵的人类弱点和麻木不仁的代表……法恩丘不愿努力去解救莉拉,他对她的战争性质的无知进行斥责,莉拉对法恩丘性无能的引用以及她对沉默的利用,在绝望的处境下既幽默又令人不安”(Podol, 1978 p 51)。“1937 年巴斯克精神之都遭到轰炸时,莉拉被困在厕所里,这在令人毛骨悚然和滑稽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感,这正是怪诞的特征。她与丈夫法恩丘的对话,暗示了他的性无能,揭露了他们相互的自私和缺乏真正的同理心,这指责了他们,但并没有减少他们困境和空袭本身的恐怖。作品中的恶棍是小说家和记者,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漠不关心,并试图利用这种情况来谋取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在最后,概括和悲观情绪被气球的象征所抵消,气球无法被刚杀害法恩丘和莉拉的士兵击落。在视觉上,阿劳巴尔利用垂直运动来表达希望和解放”(Podol, 1988 pp 134-135)。“当巴斯克人民的古都格尔尼卡在 1937 年 4 月 26 日被德国空军摧毁时,指挥这次袭击的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及其随行人员正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观望。众所周知,这次袭击的一个潜在目的,以及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国民党一方的参与,是测试新的战争技术。冯·里希特霍芬以及聚集在奥伊兹山的人们见证了第一次闪电战式轰炸的实施,这种轰炸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纳粹战略的核心。从最初的可怕时刻起,格尔尼卡的毁灭就是一个戏剧化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大多数平民受害者都是不知情的演员……当记者出现时,“阿劳巴尔对那些会从对平民人口毁灭的艺术呈现中受益的人提出了明确的指控:文学风格取代了任何准确描述所发生事件的意图;重点不再放在受苦的人民身上,而是放在假装讲述他们故事的声音上”(Drumm, 2009 pp 427-436)。
在《盛大的仪式》中,主人公“鞭打玩偶并谋杀了一个小女孩,他被专制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母亲所维持在精神病状态”(Guicharnaud,1967 年,第 185 页)。主人公的名字是伟大情人的字谜,突出了怪诞变形的强烈意味。尽管有这些模仿的元素……这部戏剧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主人公的极度痛苦……Cavanosa 患有由对母亲形象的固着引起的复杂症,这使他无法在心理上整合自己的父母或发展独立的个性和自我……Cavanosa 对 Sil 的令人发指的对待实际上是对其日益增长的害怕意识到自己压抑的欲望的反应。死亡、暴力和色情交织在一起;母亲对儿子的乱伦渴望以希望被他杀死的方式出现,并有助于解释 Cavanosa 自己扭曲的爱的感觉的本质,这在他对待玩偶和 Sil 的方式中得到了证明。身体折磨成为内心冲突的表现,而身体畸形则是精神痛苦的外化。当这些力量占主导地位时,戏剧的气氛仍然沉浸在潜意识的世界中……Lys 出现了,她是 Sil 的另一个自我(由他们共同的名字互为回文来证实);她觉得 Cavanosa 可爱迷人,因为她没有接触过其他男人……如果他的话通过暗示爱仍然只能作为以死亡告终的破坏性行为来引入一种模棱两可的意味,他对 Lys 的温柔亲吻以及他梦呓般地和她说话的事实至少部分地证明了主人公从典型的吞噬母亲的监禁影响中解放出来的希望感”(Podol,1978 年,第 65-66 页)。“不承认道德标准,生活在自己的痴迷世界中,Cavanosa 每次进入公园的另一个世界时,都会遇到一种存在和行动的方式,这与他自身完全相反……Cavanosa 的所有行为都与人们的预期相反:爱只带来他的轻蔑,任何对他表现出的爱意都会激怒他,任何对他提供的善意都会产生残酷的反应……结果是一个角色不仅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并且能够以讽刺的距离观察自己运作……与必须被告知什么才能取悦 Cavanosa 的 Sil 不同,Lys 本能地知道……Lys 是早期的 Arrabal 剧本中常见的妓女女人孩子……[Cavanosa 和 Lys 的世界] 重合。她像 Cavanosa 在情感上与母亲相连一样,在身体上与母亲相连;她做鞭子,他用它们;她画玩偶,Cavanosa ‘爱’它们。Cavanosa 的母亲是专制、虐待狂和典型的报复者。她对儿子的控制力正在慢慢减弱,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被 Cavanosa 在日常仪式中在公园里遇到的其中一个女孩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她的儿子想杀了她……她知道她的儿子没有力量杀死她,因此她非常勉强地控制着他……他对无能的恐惧部分地通过他与真人大小的玩偶的自慰活动得到缓解,而他的恋母情结焦虑部分地通过他在公园里每天的追求和谋杀他遇到的一个女孩得到缓解。然而,Cavanosa 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实际上,他的幻想就是他的现实……直到他遇到了 Lys,她能够参与他的幻想世界变成的现实。当然,Lys 只是他母亲和玩偶的替代品。她让他一劳永逸地将施加在他母亲身上以及她反过来施加在他身上的关系外化”(Donahue,1980 年,第 17-21 页)。
“将他的戏剧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通过提取 11 个主要特征来对 Arrabal 宇宙进行分类:1. 一个半梦半神话的童真王国,有时幼稚;一种带有孩子气的玩乐的准天堂,在那里孩子们淘气的游戏变成了戴着手铐和脚镣的酷刑,甚至变成了不悔改的谋杀。2. 怀旧的、头脑简单的孩子气与成人含糊不清的共存(一个对母亲着迷的英雄,有厌恶女人的倾向,是这种双重性质的典型代表)。3. 受害者面对折磨者的强迫性紧张,在神话中被戏剧化。4. 欢乐与恐惧的 rapprochement;同样,怪诞的来回摇摆相反的情绪。5. 角色倍增或雌雄同体的角色。6. 极权主义隐喻:宗教裁判所、酷刑、绝望、暴力死亡、家庭成员之间的背叛。7. 倒置的基督教、神秘的象征、亵渎、色情耸人听闻、怪异的仪式和仪式、狂野的色情和死亡的联盟;虔诚和亵渎动机的同时性。8. 幻觉中的幻觉的根本对比。9. 一种冲动、有时不连贯的风格;一种不均匀、奔流或野蛮的戏剧节奏,依赖于夸张的冲击效果。10. 奇特的光学图像:矮人、巨人、驼背、巨大的气球、机器人象棋手、鞭子、棺材、裸体和丰满的尸体。11. 神话或隐喻的底层结构,将各种深奥的连贯模式相互连接”(White,1971 年,第 99 页)。
“汽车公墓”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50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在?
精力充沛的 Lasca 鼓励精疲力尽的 Tiossido 在汽车坟场周围慢跑,而一个穿着优雅的管家 Milos 则在住在旧车和废弃汽车里的人群中接听第二天早上的早餐订单。Lasca 还鼓励他的妻子 Dila 亲吻她的顾客。当他注意到她不愿这样做时,他用尺子打了她的每一只手。当 Dila 朝着各个汽车乘客走去,准备提供性服务时,她遇到了 Emanou,他出生在马槽里,是木匠和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的儿子,他表示想与她同床共枕。“我们会转身拥抱,像两只水下松鼠一样,”他提议道。她接受了。第二天早上,Emanou 宣布警察正在追捕他,因为他向穷人吹喇叭。Milos 看到 Dila 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勃然大怒,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摔倒在地。在这一天,Lasca 和 Tiossido 的角色颠倒了,后者显得更有活力。当 Emanou 的朋友 Topé 获悉有人悬赏抓捕他时,他主动向 Lasca 和 Tiossido 亲吻以出卖他。Emanou 无动于衷,从袋子里拿出杏仁给 Topé 和 Dila。“如果警察抓住你,我们会以你的名义吃杏仁,”Dila 宣称。当 Topé 亲吻 Emanou 时,Lasca 和 Tiossido 立刻逮捕了他。Tiossido 在摆脱了这件事后,他们带走了 Emanou 去鞭打他。他随后被发现骑着一辆自行车,双臂伸直,Dila 在他被带走之前为他擦汗。第二天像往常一样开始,Milos 和 Dila 在做着他们平常的家务。
“格尔尼卡”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30 年代。地点:西班牙格尔尼卡。
文本在?
在她去浴室的路上,一颗炸弹落在了大楼上,导致 Lira 被埋在瓦砾堆下,她的丈夫 Fanchou 无法把她救出来。他试图鼓励她,但一块石头掉下来伤了她的手臂,血流不止。一位作家和一位记者赶到那里,调查格尔尼卡市各地轰炸造成的破坏。“加上我正在准备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甚至可能是一部电影,”这位作家宣称。为了帮助妻子消磨时间,Fanchou 建议他给她讲个故事。“你想听那个关于在浴室里被埋在瓦砾堆下的女人的故事吗?”他问道。为了进一步取悦她,他像小丑一样扮鬼脸,但 Lira 看不见他。她问附近的树是否还完好无损;他回答说它完好无损。当他再次试图营救她时,Fanchou 被一位军官推倒,军官阻挠了他的前进,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Fanchou 无法再做任何事,于是给了她一个儿童气球。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路过,前者推着一辆装满炸药的手推车。气球爆了,留下 Lira 抱怨她的状况。军官回来了,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笑着,然后又走了。Fanchou 问 Lira 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情人。“那会很时髦,”他断言。“你从来没想过我……当我当着朋友的面脱掉你的衣服时,你总是看起来很不高兴。”当他建议她也许会因为牧师的出现而感到安慰时,她提醒他他们是无神论者。“谁,我们?”一个惊讶而害怕的 Fanchou 问道。女人和女孩又回来了,女人背上背着各种各样的武器。Fanchou 越来越沮丧,因为无法帮助他的妻子。“都是你的错。你总是那么着迷,在浴室里读书!”他脱口而出。女人和女孩第三次路过,推着一辆装满旧枪的手推车。现在 Fanchou 建议 Lira 可能会写下她的遗嘱。当他最后一次试图救她时,他自己也被埋在地下,成为又一次轰炸的受害者。女人回来了,这次没有小女孩,她带着一口棺材。两个气球升向天空。军官试图把它们击落,但没有成功。Fanchou 和 Lira 的声音从上面传来,他们笑着。
“盛大的仪式”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60 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在?
一个驼背的卡瓦诺萨人偶然在公共公园遇到了一个名叫西尔的女子。尽管他看起来很粗鲁,但她还是同意和他在一起。她善良体贴的男朋友出现了,想要带她走,但她更愿意和这个粗鲁的陌生人在一起,直到他叫他们俩都走。她走了,但后来带着一根鞭子回来了。但他还是更加粗鲁,踢了她,践踏了她。然后他叫她在他的房子外等一个灯光信号,在那里她可以帮他移走他母亲的尸体,他说他最近杀了她。然而,他的母亲并没有死。她恳求他远离女人,因为女人只会偷他的钱。他坐在她膝盖上,然后送给她一个小棺材,里面放着一个娃娃。她称他为怪物,他对此表示轻蔑。她接下来要求看他手中的刀,然后要求他用刀刺她,但他做不到。他们似乎有所和解。然后她在他的嘴上咬了一口,开始回忆往事。“还记得有一次,你不让我没有你陪同就出去,你就把你的手钉在了通往外面的门上,威胁说要那样一直待着,直到我回来,”她提醒他。她注意到他的床单底下伸出了两条腿,他解释说那是他习惯抚摸的玩偶之一。母亲离开后,西尔敲门进了房间。当卡瓦诺萨把她打扮成基督形象时,她同意为他而死。她也注意到床单底下伸出的腿。那不是玩偶,而是一个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死女人,她帮着把这个女人抬到屏风后面。西尔的男朋友再次出现,西尔向他解释了她在房间里做了些什么,但她把屏风拉开,准备让他看看尸体,却发现尸体不见了。卡瓦诺萨突然出现,抓住男朋友,把他绑起来,威胁他,但最后还是放了他。母亲回来了,在窗外看着警察带走一具尸体,卡瓦诺萨解释说那是他前天杀的。 “我告诉过你不要把她留在地窖里,”她责怪他。卡瓦诺萨想让西尔离开,但她坚持要留下来,直到他同意把她变成她母亲的奴隶。第二天晚上,他遇到了另一个名叫莉丝的女人,她的性格和西尔很像。他也对她很粗鲁,但她仍然想和他在一起,从裙子下面拿出一根鞭子给他。他决定从他的车里拿出一个娃娃,和她一起离开。
让-克劳德·布里斯维尔
[edit | edit source]在后荒诞主义戏剧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包括历史剧的回归,尽管在让-克劳德·布里斯维尔 (1922-2014) 的《笛卡尔先生与帕斯卡尔先生的对话》(1647 年,两名数学家和哲学家唯一一次会面的基础) 中,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布里斯维尔还创作了两部历史剧:《晚餐》(1989 年),以 19 世纪政治家塔列朗与警察部长约瑟夫·傅歇之间的冲突为基础;《侍从室》(1991 年),以玛丽·杜德凡伯爵夫人与朱莉·德·莱斯皮纳斯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由于眼睛失明,伯爵夫人把她哥哥的私生女朱莉接到了她家,让她当她的读者。伯爵夫人的房子最初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直到她与朱莉接受的更自由的理念疏远,而朱莉的侍从室引起了她保护者的嫉妒,迫使她离开。
《笛卡尔先生与帕斯卡尔先生的对话》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647 年。地点:法国巴黎。
文本在?
勒内·笛卡尔遇到了布莱兹·帕斯卡,这两位数学家和哲学家对宗教特别感兴趣。笛卡尔承认,到目前为止,他知道表达宗教观点的风险,他一直“戴着面具前进”。与笛卡尔不同,尽管帕斯卡在数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他开始对科学失去兴趣,因为他正在寻找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提供的确定性。帕斯卡对笛卡尔对数字的信仰感到愤怒。“一个基督徒能这样推理吗?”他反问,“难道你没有看到理性会让你不再需要上帝吗?”笛卡尔否认了这一点。帕斯卡害怕上帝和他摇摆不定的缺乏信仰,他只希望为自己的救赎而工作,而笛卡尔对此充满信心,同时也在研究科学问题。帕斯卡请他写一封信来支持一位被耶稣会士错误指控的詹森派同仁,耶稣会士是当时的统治派别。笛卡尔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卷入不必要的宗教争端。帕斯卡感到失望,指责他胆小,笛卡尔否认了这一点。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萨布莱夫人在领圣餐的同一天晚上跳舞的决定,笛卡尔认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帕斯卡却对此感到震惊。帕斯卡进一步疏远了他的同行哲学家,宣称他欢迎磨难,因为肉体的痛苦“把我与基督联系在一起,”他说。笛卡尔对帕斯卡的禁欲感到沮丧,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个男人曾经救过他性命的故事,当时他被困在马下面,很可能会冻死。那个男人,尽管他很慈善和善良,后来却因为帕斯卡指责他信仰古怪而失去了他作为教士的职位,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穷人:这是侍奉上帝吗?笛卡尔最后认为,与地狱危险有关的事情是可辩论的,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帕斯卡不同意。“我所追求的一切都超出了数学,”他断言。
贝尔纳-玛丽·科尔特斯
[span>edit | edit source]在后现代时期,贝尔纳-玛丽·科尔特斯 (1948-1989) 的《重返沙漠》(1988 年) 也值得注意。
在《重返沙漠》中,“玛蒂尔德的到来”扰乱了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所有事物:家庭内部的关系,亚德里安被保持在依赖状态,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特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以及城外的人际关系,当地权力的俱乐部式联系将被打破。玛蒂尔德部分出于纯粹的固执,部分是因为她想重新获得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部分是因为她对第一任妻子玛丽的死感到真正的沮丧,才引发了这场革命……玛蒂尔德和亚德里安只能通过以物易物来相互联系,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房子和工厂一样,变成了商品”(布拉德比,1991 年,第 276-277 页)。“暴力在每个场景中都潜伏着,从一开始玛蒂尔德·瑟佩努瓦兹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她的祖传家园,就无法和她的尊敬的资产阶级兄弟亚德里安打招呼,而不互相辱骂。这个场景很有趣,因为亚德里安对中产阶级尊严的虚假主张与他和姐姐之间实际上爆发的恶性狗咬架之间存在着讽刺的距离。这出戏中的暴力始终以讽刺的视角呈现。在戏的结尾,城里的领导人(包括亚德里安)参与了一个成功的阴谋,在阿拉伯咖啡馆里放置炸弹。当炸弹爆炸时,亚德里安自己的儿子正在里面寻找性冒险,当他浑身是血地回家面对他的父亲时,亚德里安所能做的就是因为他不经允许离开家而打他”(布拉德比,1994 年,第 377-378 页)。
“流亡者、外国人、局外人是在科尔特斯的戏剧景观中生活着的[陌生人]。他那么多角色可以说是四处逃窜,离开了祖国,来到一个他们的差异既明显又清晰的国家。玛蒂尔德在《重返沙漠》中质疑她的祖国。“我属于哪个国家?”她问道。“也许你的家是你不在的地方?”……玛蒂尔德注定要在一片她徘徊在外国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景观中游荡。她最初以从阿尔及利亚不断升级的冲突中逃出来的难民身份出现;15 年前,她离开梅斯,因为她被她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公开羞辱;在剧本的结尾,她再次离开梅斯,带着她争吵不休的哥哥一起离开……对于马修来说……家庭仅仅是关于遗产;强迫性的结构,在那里厌女症从父亲传给儿子,孩子在“踢打和明智的训诫”中长大,父亲永远被困在破坏性的青春期,一生都在和学校的朋友们沉迷于阴谋游戏……在科尔特斯创造的世界里,男子气概被揭露、伤害、陷入困境,受到威胁。在《重返沙漠》中,它是通过亚德里安的印象派儿子表达的,即“打别人的脸……一起喝酒和打架的伙伴……要杀要征服的敌人。”它的运作方式被揭露和嘲弄,就像第九幕中城镇官员(由警察局长、律师、部门长官和亚德里安代表)在密室里策划反对那些质疑他们过度的行为”(德尔加多,2011 年,第 28-31 页)。
“科尔特斯的戏剧与当代戏剧写作中以叙事驱动的传统相去甚远。他角色的行为总是令人惊讶,抵制心理因果关系的运作,而心理因果关系是许多现实主义戏剧的核心。科尔特斯的戏剧颂扬不可预测性和未言明的部分;他们对与方法演技通常相关的对角色的现实主义描写有一种反感”(德尔加多和布拉德比,2015 年,第 141 页)。
《重返沙漠》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60 年代。地点:法国。
文本在?
在阿尔及利亚缺席十五年后,玛蒂尔达带着她的女儿法蒂玛和儿子爱德华回到了法国,住进了她哥哥阿德里安留下的房子。阿德里安以为她只是短暂地回来,并非如此,正如她从一开始就说明的。她打算住在属于她的房子里,就像工厂属于他一样,这是他们父母去世时决定的。阿德里安很不高兴,因为他负责对房子进行了改进,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他,但仍然被迫接受。当他的儿子马修坚持要继续拥有自己的房间,而不是和爱德华合住时,他打了马修的脸。法蒂玛向她的母亲承认她在花园里遇到了一个人,但当被问到是谁时,她拒绝说出。在花园里,阿德里安发现马修试图离开家族领地,加入法国军队参加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我不想继承,”沮丧的马修宣称,“我想在说出优美的语句时死去。”阿德里安阻止了他。看到一位名叫普兰特斯的警官出现在房子里,爱德华跳到他身上并把他制服了。这个困惑的男人问玛蒂尔达这样做的意义。她回答说,十五年前,这个人是她被流放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指责她未婚生子,有伤风化。为了羞辱他,她剪掉了他的头发。看到他这样暴露无遗,阿德里安建议,被羞辱的警官可能会报复,跟踪法蒂玛并把她关起来,说她疯了,更何况她还假装看到了他已故妻子的幽灵玛丽。阿德里安和玛蒂尔达因为他们各自的需要而发生争吵,涉及多个话题。阿德里安尤其担心爱德华如何鼓励马修去阿拉伯咖啡馆跟着他。阿德里安打了玛蒂尔达,玛蒂尔达还击。他们被爱德华和一个仆人阿齐兹分开。在花园里,马修试图和法蒂玛发生性关系,但被她拒绝了。玛蒂尔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鼓励马修继续与她的两个孩子保持友好关系。一个心烦意乱的法蒂玛指着一个看起来像玛丽鬼魂的东西,但她母亲什么也没看到。晚上,玛蒂尔达和她的女儿在床上,她告诉女儿,她觉得在哥哥家里有危险。她特别想知道玛丽是怎么死的。阿德里安进来告诉他们,马修已经参军了。他对他儿子能否活着从战争中回来没有信心。当法蒂玛表达了她想回到阿尔及利亚的愿望时,玛蒂尔达没有回答。阿德里安深夜与普兰特斯和律师波尼会面,等待他们炸毁阿拉伯咖啡馆的炸弹的消息。令他们惊恐的是,爆炸炸死了马修和阿齐兹。阿德里安和玛蒂尔达决定搬到阿尔及利亚,远离这栋像沙漠一样的房子。
雅丝敏娜·雷扎
[edit | edit source]
雅丝敏娜·雷扎(1959-?)仍然延续着荒诞主义传统的风格,创作了“艺术”(1994)。“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戏是对现代艺术市场的讽刺,[另一方面]仅仅是探索友谊的考验和磨难的借口”(格林,2020年,第266页)。
“雷扎在紧张、巧妙的结构和经常令人捧腹的场景中探究了艺术和感情的暧昧性......艺术作品是否有内在价值,或者价值是由市场、时代还是观众的突发奇想创造的?是否有无私的友谊?...雷扎用外科医生的精准度来衡量她角色的气质,剧本中不断变化的愤怒、怨恨和同情的潮流在一场基本上是一场长篇讨论的戏剧中创造了惊人的悬念。对话具有光学错觉的悖论般的多功能性:塞尔吉、马克和伊万通过批评艺术来批评对方,每个人在攻击对方时都会出卖自己。他们对文字和概念的争论(是画中的白色,还是白色的概念,是如此令人不安?) 可以让他们加入解构主义者的会议”(温,1998年,第2页)。
“塞尔吉在马克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中看到了价值。而这种威胁破坏了他们的友谊......西方思想中最早对友谊的概念之一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他所称的性格友谊或品格友谊的概念。这不是唯一存在的友谊类型——还有基于权宜之计等因素的友谊——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性格友谊是最高级的友谊。这是存在于平等者之间,具有相同美德和卓越的人之间的友谊......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没有朋友,没有与我们平等的朋友,我们就无法客观地评估我们自己的品质,也无法客观地衡量我们是否具有美德或卓越。真正的自我认知需要一个外部视角来验证它......现在,如果我们假设马克和塞尔吉之间的友谊是这种类型,那么就更容易理解马克的激烈反应。从马克的角度来看,塞尔吉对这幅画的难以理解的欣赏意味着塞尔吉和马克不是彼此的化身,这当然威胁着马克,然后也威胁着塞尔吉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如果马克和塞尔吉要维持他们的友谊,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建立共同的感知能力。马克必须在塞尔吉的画作中看到某种价值。当然,这发生了,尽管经过了一系列非常奇怪的事件......比喻地说,友谊促使马克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塞尔吉看到的地方找到价值,尽管不是以塞尔吉的方式,但这使得他们的友谊得以恢复,强调了艺术不仅可以确认友谊的存在,而且还有可能扩大友谊的卓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另一个自我的感知能力的卓越性”(卡罗尔,2002年,第200-206页)。虽然马克对这幅画的新看法可能是真诚的,但他的新观点也可以被解释为“放弃对权力的渴望”来确保友谊(卡沃夫斯基,2009年,第78页)。
“皮肤科医生塞尔吉怀有艺术和智力方面的野心;航空工程师马克更脚踏实地,发现这幅画的购买,他明确地称之为‘那块狗屎’,很可笑。这两个男人,每个人都在他们选择的职业中获得了成功,把第三个角色伊万拉进了他们的争论。伊万卖文具,而且是一个相当笨拙的拖延者。显然,这出戏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情节,以及它提出的各种问题:友谊是否能够经受住个人固执或社会分化的考验;安特里奥斯是否可以被归类为‘艺术’作品;这些‘单身汉’(一个是离婚的,一个是婚姻出现问题,另一个即将结婚——他的婚礼在戏剧进行期间在幕后举行)是否能够建立持久的关系。这出戏也不仅仅是其组成主题的总和,尽管这些主题对大西洋两岸的观众来说都很熟悉:友谊的脆弱性,势利,金钱,攀附权贵,孤独,追求幸福,以及现代艺术的煽动性作用”(雅克马尔,2013年,第234页)。
这部戏“围绕现代男性友谊的权力动态和情感扭曲的揭示而构建。随着情节的发展,所有角色都严厉地批评了对方的情侣、事业和家庭缺陷。贯穿始终,这场战斗都时刻关注着这幅画,直到塞尔吉邀请马克用伊万的笔之一去毁坏它。他们的关系,‘被言语和行为摧毁’,在塞尔吉所说的‘试用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戏剧以马克重新审视这幅画,不再看到一片白色,而是看到‘一个穿过空间然后消失的人’而结束。这部戏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艺术的分裂力和调和力的悖论:通过对这幅画的意见分歧,这些男人解构了然后重建了他们的关系,并以尖刻的智慧,以及在某一点上的身体和言语暴力”(盖尔,2015年,第197-198页)。
"艺术"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90年代。地点:法国卢瓦雷省。
文本在 https://pdfcoffee.com/art-yasmina-rezapdf-pdf-free.html http://pvp.org/Play%20Reading/ART%20by%20Yasmina%20Reza.pdf https://kupdf.net/download/art-the-play-yasmina-reza-english-pdf_59f0c2bbe2b6f598324f005f_pdf
塞尔日买了一幅安特里奥斯创作的昂贵画作,画作以白色背景上白色的线条构成。他的朋友马克对塞尔日缺乏判断力感到非常沮丧。为了缓和气氛,马克笑了,但塞尔日没有。当马克向他的另一个朋友伊万宣布了这笔购买时,伊万并没有那么生气。伊万甚至对塞尔日说他喜欢这幅画。塞尔日伴随着伊万开怀大笑。塞尔日告诉伊万,马克的笑声是“讽刺的,没有魅力”。当伊万向马克报告他们的谈话时,马克明确表示塞尔日只是为了取悦他而笑,而不是出于正确的理由,因为这幅画很荒谬。塞尔日向马克报告伊万喜欢这幅画。马克报告说他有点改变了主意,问自己:“屈服于这毫无逻辑的购买,难道不是一种高度诗意的姿态吗?”伊万即将结婚,但与他的女朋友在婚礼邀请卡上发生了冲突。她希望她的继母被列入邀请卡,但由于伊万讨厌自己的继母,他拒绝让她被列入。马克和塞尔日一致认为他应该取消婚礼。但伊万说他不能,因为他的老板是女方叔叔。马克对伊万的态度感到恼火,“因为他是一个小妓女,”他说,“卑躬屈膝,被金钱愚弄,被他认为是文化的东西蒙蔽了,我绝对要呕吐的那种文化。”这时,塞尔日挑战马克。“你有什么资格制定法律?”他咄咄逼人地问道。另一方面,马克无法接受塞尔日喜欢他购买的画作,而塞尔日则愤慨于马克从不被他自己的意见所伤。塞尔日明确表示,他从未对马克的女朋友说过负面评价。当马克坚持要求他的朋友改变对他女朋友的看法时,他拒绝了。他们发生了争执。在争斗中,伊万不慎被打中了耳朵。他们停下来照顾他。最后,马克揭示了他对这笔购买如此生气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不能再以塞尔日的导师的身份来代表自己,用塞尔日的意见来衡量所有事物。为了证明他认为友谊比画作更重要,塞尔日允许马克用记号笔毁坏这幅画,这让伊万感到震惊。马克的渲染改变了他对这幅画的看法。他现在在这抽象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价值,尽管与塞尔日的观点不同,但它使他们更加亲近。塞尔日和马克能够修复损坏。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可能损坏的画作可以修复时,马克承认他并不认为可以修复。塞尔日撒谎说他也不认为可以修复。
让-玛丽·贝塞
[edit | edit source]
让-玛丽·贝塞(1959-?)创作的《精英学校》(1995 年)以更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撰写,讲述了发生在知名商学院学生之间互动的故事。
"精英学校"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90 年代。地点:法国巴黎。
文本在?
深夜,阿涅斯为自己准备茶水,保罗加入了她。她怀疑伯纳德、路易-阿诺德和维厄斯,保罗的室友,密谋在周末离开公寓,以便保罗能够把她弄到床上。特别是,她猜测是路易-阿诺德建议保罗给她打电话。她提议一个交易:他们两个人中谁先能勾引路易-阿诺德?如果她赢了,她和保罗将在他们自己的公寓里住在一起;如果他赢了,她会离开他。后来,当阿涅斯和她的朋友埃梅琳等待男学生到来时,她们争论着关于一起谋杀案的当前事件的解释。埃梅琳离开时,伯纳德提着一个沉重的包裹走了进来,解释说路易-阿诺德落后是因为他在慢跑。令她们惊恐的是,路易-阿诺德带着沾满鲜血的侧面走了进来。保罗加入他们两人,帮助他们的朋友前往医院。当伯纳德和保罗学习时,前者无法集中注意力,离开了房间,因为后者只能哲学地思考发生在路易-阿诺德身上的事情。当后者穿着浴袍以发烧的状态进入时,他也把保罗的思想斥为毫无新意。尽管如此,路易-阿诺德还是试图帮助保罗完成学业。“真正能帮助我的是,”保罗说,“你处理这个案子,然后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对他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想法。凌晨 3 点,路易-阿诺德惊讶地看到阿涅斯走进他们的公寓,门被粗心地留着没有锁。阿涅斯提醒路易-阿诺德,他在医院床上向她表达了温柔的感情,而且是她,而不是他的朋友埃梅琳,去看望了他在医院。当他们即将接吻时,埃梅琳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吓了一跳,她独自睡在那里,暂时代替了缺席的室友维厄斯。“我以为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埃梅琳宣称。“这并不赋予你制造场景的权利,”他回答。“性会捆绑,但不会固定,”阿涅斯宣称。“我不跟你说话,”埃梅琳反驳道,然后在看到路易-阿诺德对继续讨论不感兴趣时离开了。他离开了,然后又回来了,带了一些钱,这样阿涅斯就可以回家了,但她拒绝了。他撕掉了钞票,扔在地板上。她捡了起来。当伯纳德回到公寓拿遗忘的讲义时,他发现有一个陌生人梅西尔,保罗的明显床伴。当梅西尔离开去他们的公寓洗澡时,路易-阿诺德问保罗是否会加入阿涅斯去她学校参加周六晚上的聚会,因为他已经收到了邀请,但保罗不确定自己是否也被邀请了。路易-阿诺德突然退缩,并举起椅子自卫,因为他看到梅西尔从浴室里出来,因为梅西尔就是刺伤他的人,现在正迅速消失。后来,埃梅琳告诉保罗,路易-阿诺德将离开他的公寓,搬到其他地方住。当路易-阿诺德出现要搬走他的东西时,保罗讽刺地列举了他未来商业生涯的优势。路易-阿诺德没有回应,而是和埃梅琳一起前往她的公寓。阿涅斯告诉保罗,她差点同意和路易-阿诺德睡觉;反过来,保罗告诉阿涅斯,他自己成功地和路易-阿诺德睡了。她认为他可能在撒谎,但无论如何都离开了。
吉尔达·布尔代
[edit | edit source]吉尔达·布尔代(1947-?)仍然以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了《加油站》(1985 年)。布尔代还创作了《月球的吐口水》(1986 年)。就像比汉的《人质》一样,故事发生在一个妓院酒吧里,那里有一个保守的老板、一名士兵和两个同性恋。皮条客雷格洛威胁要把他的妓女,姓公主,送到更糟糕的地方,因此她试图通过割腕自杀。一个担心错过火车船班次,无法与他的小队一起前往海外的士兵,一个失败的摇滚艺术家香蕉,以一种超然的方式评论着行动,一个富有而疯狂的麻烦制造者,打嗝,他挑战着所有人,以及一个受到另一个皮条客保护的妓女,帕基塔,构成了这个令人不快的群体的一部分。与 20 世纪后期普遍存在的以非现实主义戏剧结构呈现现实主义对话的趋势不同,例如,角色直接与观众对话,布尔代以现实主义戏剧结构呈现现实主义对话。
“加油站”
[edit | edit source]
时间:1980 年代。地点:法国机场附近。
文本在?
在一条最近被封锁的道路上的加油站,一位名叫 Samson 的修理工正在修理一辆标致汽车。与此同时,Theresa 的智障儿子 Tut-Tut 正在角落里小便。Theresa 是一位老师,是 Madeleine 三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不幸的是,尿液溅到了正在汽车下面修理的 Samson 身上。一位名叫 Winnock 的骑摩托车的人希望 Madeleine 的小女儿 Doris 和他一起离开法国,但 Doris 还没有成年,需要她母亲的同意。离考试还有 15 天,Doris 甚至不愿意向她母亲提出要求。一位陌生人找到 Samson,请求使用电话。这个陌生人名叫 Humbert,他希望与 Madeleine 通话,Madeleine 是他的妻子,也是加油站的老板。18 年前,Humbert 抛弃了 Madeleine,现在他不愿空手而来,他告诉 Madeleine,自己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因为肺部患了癌症。他希望在去世前与 Madeleine 处理好财务问题。与此同时,Madeleine 的二女儿 Maud 曾经离过婚,正在和她的未婚夫 Thomas 讨论结婚计划。Thomas 是一位医科学生。然而,Thomas 离开后,Maud 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男人,安排秘密约会。Maud 和 Doris 遇到了他们的父亲,他再次解释说他回来是为了避免在他死后出现法律纠纷。Humbert 向 Maud 和 Theresa 详细说明,他离开家是为了成为一名画家,现在拥有 100 幅可能很有价值的画作,打算将这些画作留给她们。在他有生之年,Madeleine 无法在没有他同意的情况下出售加油站。无处可去,Humbert 便前往 Tut-Tut 在树林里的小屋。第二天早上,Maud 在汽车里醒来,她身旁是她的情人 Richard。除了 Samson,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Samson 讽刺地将 Maud 的内裤和长袜挂在汽车的天线上。Doris 告诉她母亲,她想在 Maud 婚礼之前离开家。在森林里度过一夜后,Humbert 又添加了一个解释他离开的原因,18 年前,他发现了妻子与她情人之间的信件。Madeleine 感到惊讶,但毫无悔恨,她拒绝了 Humbert 住在她家直到他去世的愿望。Winnock 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因为 Doris 没有在他们约定的地点出现。然而,他很高兴拿到了 Doris 父亲的书面同意书,这使得他们可以前往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参加摇滚音乐会。然而,Madeleine 拒绝给出她的同意,直到 Doris 获得高中毕业证。Richard 回来寻找他遗失在汽车里的钱包和刀子。Theresa 并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她的妹妹的情人,她坐上了 Richard 的车去为她的姐姐购买结婚礼物。在婚礼前夜,Thomas 对 Maud 的婚纱赞不绝口。然而,Thomas 一离开,Maud 就再次打电话给 Richard,但她只能打到他的语音信箱。“是我,又是你,”她在电话里说。“我渴望你,渴望我们。我需要你,我们必须见面。”当 Richard 突然出现,告诉她他打算加入他朋友在塔希提岛开设的视频店时,她感到很惊讶。尽管如此,Richard 仍然想要她,犹豫之后,Maud 也想要他。然而,Pinnock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准备前往西班牙。但 Doris 看到 Richard 之前和 Theresa 在一起,现在又和 Maud 在一起,感到很惊讶,她此刻不想跟随 Pinnock。Maud 担心 Richard 在和 Theresa 做什么。因此,她大量喝了茴香酒,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进树林去见她的父亲。与此同时,Samson 已经修好了汽车。在婚礼当天,Thomas 发现只有 Richard 和 Theresa 的客人以及大量挂在墙上的抽象画,感到很沮丧。Thomas 认出 Richard 的车,因为几天前,这辆车曾经在他面前鲁莽地行驶。整个家庭迟到了 15 分钟,才赶到市政厅,但 Maud 的婚纱破了,而且很脏,Humbert 的衣服也因为在树林里躺着而沾上了泥土。Thomas 非常生气,抓住 Maud,Maud 于是打电话给 Richard 求助。当 Thomas 问她为什么打电话给婚礼上的客人求助时,Maud 坦白说 Richard 已经是她几个月的情人了,Theresa 听到后感到震惊。Thomas 威胁 Richard,Richard 拔出刀子,Thomas 则拿起了传动轴,过分兴奋的 Tut-Tut 则向 Richard 泼汽油,Madeleine 拿出打火机阻止这场争斗。Thomas 对整个事件感到厌恶,他将戒指扔在 Maud 的脚下,然后离开。Madeleine 打算关店,她将标致汽车送给了 Samson。Samson 需要考虑一下。Richard 仍然有可能让 Maud 加入他。Theresa 认为 Richard 的评论对她的女儿很不礼貌,但她仍然无法抗拒这个男人。Doris 仍然不确定是否要跟随 Pinnock。
